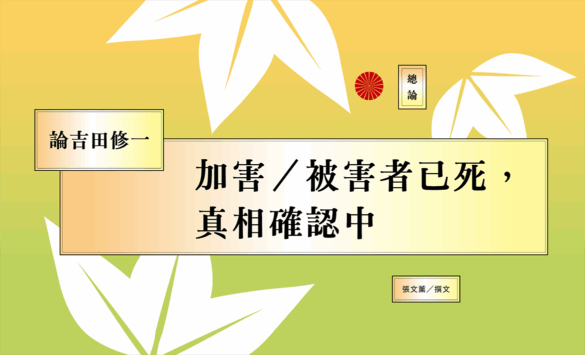二〇一〇年代中期,台灣文壇掀起一波台灣文學獲得日本文壇青睞的現象。二〇一五年東山彰良《流》獲得直木賞、二〇一七年五月出版的《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獲得讀賣文學等三項大獎,二〇一七年溫又柔《中間的孩子》入選芥川賞,二〇一七年李琴峰《獨舞》獲得群像新人文學獎、二〇一九年《倒數五秒月牙》入選芥川賞、二〇二一年《彼岸花盛開之島》獲得芥川賞。比起台灣人能用純熟的外語寫作、並獲得國外大獎的青睞,「台灣」能在國外持續成為注視焦點這件事,在長期以亞細亞的孤兒自況的台灣人眼中,可能更為驚喜。
這波風潮的開端,應該從二〇〇九年吉田修一《路》開始連載算起 ㊀。 吉田修一比起東山彰良、溫又柔、李琴峰成名更早,二〇一〇年由妻夫木聰主演的《惡人》上映之前,即在台灣擁有大量讀者。在大眾小說的形式中包裹著芥川賞文學主題的《惡人》㊁, 以一則發生在九州最大都市福岡的殺人事件為開端,嫌犯在九州各地逃亡將近一年,最後結束在九州邊陲的廢棄燈塔。雖然歷經四季,但《惡人》中的九州盡是酷寒陰冷景觀,正如故事裡的犯罪關係人雖曾接受種種偶發的善意,但結局幾乎沒有光。
九州明明與台灣氣候相似,圍繞市區的小山遍佈常青闊葉樹,空氣中飽含水氣,冬天幾乎不下雪。吉田修一本身是九州人,在長崎出生,十八歲之後至東京求學後居住至今。這樣的遷移方式與大多數台北人類似,可能因為如此,吉田修一小說繁體中文版的作者介紹,總強調他在「描寫年輕人在都會生活的當下心情」,以「不屬於東京、不屬於故鄉」的心境為主題,應該成功地喚起許多北漂青年的心緒。不過,在日本近代文學中,以故鄉喪失為主題的小說多如繁星,從夏目漱石《三四郎》到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都可以算進來。與許多誕生在北漂文青租屋處的台灣都市文學不同,吉田修一筆下的台灣溫暖而明亮,連高溫悶濕的夏天都是適合重逢的熱戀季節。在《惡人》、《國寶》中把九州寫得那麼冷,卻在《路》中把台灣鐵皮屋的夏夜寫得舒適宜人的吉田修一,肯定在離鄉上京求生存的年輕人身上,看到了些別的。
吉田修一在《路》中把光亮都給了台灣。卻把《惡人》、《國寶》㊂ 關鍵的殺人事件,留給了九州罕見的大雪天。要列出年表後才能發現,《惡人》、《橫道世之介》㊃、 《路》這三部主題、舞台、類型都不重複的長篇,時間上幾乎是一部接著一部接連寫成的。從《國寶》回看,會發現家族離散的迷惘少年、奮不顧身的友情、自私的背叛、陌生人的善意、犧牲與救贖等主題形象,都在這三部中迴旋出現。《國寶》為少年們提供了「藝」的琢磨作為出口,在結尾的《阿古屋》(電影版改為《鷺娘》)舞台上,將現實人生的貪與瞋,轉化為角色的痴,肉身也在樂舞結束之際化入白雪茫茫的虛空。
《國寶》的喜久雄在第一次業餘扮女形的宴會中遭遇殺父之仇,並且是由信任的叔父所下的毒手,這令人聯想起〈哈姆雷特〉或《義經記》的故事開頭,讓主角脫離原本已設定好的人生進路,並被賦予體驗複雜人情的機緣。吉田修一並沒有塑造出復仇王子,而是將他丟入充滿體現人性之背叛與慾望的「人情」世界。「人情」與「緣」是相對概念。當與原本應照拂、支持個體的血緣、地緣關係者之間的連結驟然斷絕,孤身處於廣漠世間的個體該如何存活?他人的情感是否能取代與生俱來的血緣?
《國寶》設計了最依靠血緣、地緣來支撐的傳統藝能歌舞伎與黑幫,從戰後初期、經濟起飛、泡沫經濟破滅的時間序,探討日本社會中的封閉性與排他性,對於個人心性的琢磨與扼殺。喜久雄與俊介,傳統藝能中的外來者與嫡傳子的相對設定,其實在宮藤官九郎《虎與龍》(落語)、《我家的故事》(能樂),以及動漫《昭和元祿落語心中》都有類似的人物構圖。現代與經典劇目之間的對照,襲名秩序的鬥爭與失落,這種取材自江戶傳統藝能的現代人情劇,顯然是創作者用來表現對於個體與社會之觀察的絕佳型態。
《惡人》中的殺人犯被母親棄養、脫離老家獨自在福岡生活,與《怒》中的殺人犯、二名謎樣男子、被美軍侵犯的少女一樣,都是現代社會中的「無緣者」。《惡人》中最常被引用的,是被殺害者的父親佳男,對將女兒拋棄在山路上的增尾的友人鶴田所說:「現在這個社會上,連珍惜的對象都沒有的人太多了」的那段話(p.358)。鶴田原本與增尾一樣,都是游手好閒、經濟寬裕的年輕人,但在見證佳男喪女的悲傷、增尾與其他朋友的無動於衷後,產生了變化。
以往我總是關在房間裡埋頭看電影,我看過太多人哭泣、悲傷、憤怒、憎恨的模樣了,可是那個時候,我頭一次感覺到人的感情有味道。
像是增尾把佳乃踢出山路時的腳底觸感、佳乃被踢出去時手掌按在地上感覺到的冰冷,再者,像是佳乃被兇手勒住脖子時看到的天空情景,或是兇手勒住佳乃脖子時的觸感⋯⋯ ——《惡人》p.350-p.351
《惡人》從被害者的雙親與友人、加害者的家人等事件周邊關係者的角度,一步步迫近當天深夜,被害者與加害者,如何走進無可挽回的死亡隧道。讀者看到的不僅是殺人行為的可惡,更發現佳乃的自私、不把佳乃生死當一回事的增尾,也都在這起悲劇中扮演關鍵角色。但這些人個性中的缺陷,卻不能視為悲劇發生的必然性。殺人者對先拋棄自己、卻又被人拋棄而獨行山路的佳乃的善意,逃亡過程中吐露自己必須勒索母親的理由是「⋯⋯可是那樣的話,兩邊都不能變成被害人了。」(p.373)這些原為體諒對方的不堪與自私,卻在種種偶然交織下導向悲劇的情愫,可恨卻可憐可愛的,正是「人情」。
《惡人》、《橫道世之介》、《路》、《怒》到《國寶》,都在對照大眾媒體上的真相與真實之間的關係。《惡人》的真相是交友軟體上相識的男女情殺,但在真實這邊,被害者的父親佳男的心情卻是「有個兇手殺了自己的女兒。有個傢伙踐踏了女兒的愛情。應該憎恨的應該是兇手,但是浮現在腦子裡的卻淨是女兒被踢出車子的景象。」(p.316)真實是對方原想撫慰獨行山路的女兒,她將自己的不堪與怒氣轉發在對方身上;最可恨的到底是誰?那個「踐踏了女兒的愛情」的增尾,得知女兒死亡仍不以為意的增尾,才是最可恨的「惡人」吧?被害者的遺屬佳男的話語無法讓女兒重生,但至少改變了鶴田,讓他「頭一次感覺到人的感情有味道」。這種不合理、不合法的行為動機與動人的渲染力,正是江戶文藝精髓「人情」之所在。
其實以大學校園生活為舞台的《橫道世之介》,主角名字也來自江戶文藝——井原西鶴的浮世草子《好色一代男》。井原西鶴還有《好色五人女》等作品,以「好色物」見稱。吉田修一顯然擷取了井原西鶴筆下的「色」等於人情義理,而不僅限於男女愛慾的精神,讓來到東京念大學、脫線而笨拙的橫道世之介,在社團、打工、租屋處以及偶遇而生的友情與戀情中成長,卻仍保留著奮不顧身助人的熱血與善良。世之介在四十歲那年為了救陌生人而被電車輾斃,這是發生在東京的真實事件,吉田修一寫出的是這令世人驚奇的一則新聞中,保留著泡沫經濟後仍留存的高尚品格。而這在朋友心中留下「一想到這世上有許多人在青春年少時沒遇見過世之介,不知為何,總覺得自己值得了」(p.354)有趣的是,因死亡而消失在日本社會的橫道世之介形象,卻成為《路》的主旋律。
春香常想,有這種氣氛的地方,在東京似有實無。這裡不像澀谷的中央街那麼熱鬧,也沒有下北澤那麼洗鍊,但舉個例來說好了,對,就像夏天廟會過後,錯過回家時間的年輕人在廟裡殺時間,在台北這裡,經常能感覺得到那種氣氛。 ——《路》,p.37-p.38
《路》的主軸是日本人來台灣建設高鐵的真實事件。日本女孩春香多年前來台旅行邂逅台灣男孩人豪,因為對人豪的好感而來台工作。春香與上司安西,對照著現在在東京上班的人豪、高雄燕巢的高鐵技術員工威志美青夫婦,同年齡層的日、台青年在高鐵從建設到成功通車的過程中,交織出明亮而溫暖的南國台灣形象。
《路》中的台灣年輕人對總統大選積極熱情,選後的虛無失落、服兵役、騎長途機車衝墾丁、花蓮,會因為擔心牽掛而在沒有聯絡方式的情況下衝到地震後的神戶,也會把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場面話的「隨時歡迎到我家來」當真。這些不問回報的善意與真誠,甚至延伸到戰前的殖民歷史,讓台北高校的老同窗呂醫師,原諒勝一郎出於自私的「二等國民」蔑稱。
對照起來,日本的同齡青年則是罹患憂鬱症、計較孩子的升學問題、倚賴父母出面解決女友懷孕等等,雖然「認真又溫柔」卻「像個小孩子」(p.110)一般,困在眼前的時間中。在《路》中,可以發現「時間」對於吉田修一所詮釋的「人情」的重要性。「守時」是日本交通建設的最優先準則,高鐵的日台合作往往在準時通車、準時發車之間產生爭議。《橫道世之介》的主角死於快速通過的列車軌道上。《路》的日本人角色,則都因為必須過著與眾人一致、「理所當然」的人生而痛苦。
相對的,擁抱「預定就只是預定啊。有延誤的時候,自然也有提早的時候。」(p.250)的台灣,則因為這些無法精準預測而多出來的時間,產生的更多可能性。《路》中的台灣人對於外來者、對於沒有地緣關係的觀光客,都可以自在相處。而原本在日本已奄奄一息的個體,也因為時間觀的改變而重獲新生。「從日本帶來的時間流動,不知不覺間慢慢被同化成台灣這裡的時間流動了」。(p.287)台灣的人情甚至改寫了殖民時代「同化」的意義,決定死在呂醫師醫院的勝一郎,是以「回到台灣」的姿態來詮釋自己錯過的戰後光陰。
台灣在日本觀光指南中,常以「人情之地」(人情の町)來指稱。在《路》中,連火車窗外「晾在屋頂的衣物、巷弄間穿梭的摩托車」這種缺乏公共意識的表現都能成為風景。這最美的人情風景,讓「沐浴在南國陽光下的樹木,彷彿以濃烈的綠色大聲宣告自己是活著的⋯⋯活著就是這麼簡單,正因為簡單,才如此強勁」(p.257)。對照雖然也種植了許多樹木,卻都是「有氣無力」的熱海療養所(p.258),春香與勝一郎,都在台灣的人情與多出來的時間中,獲得救贖。
然而,這種對於南國陽光的憧憬,是否正如台灣人嚮往純白雪山風景一樣,都來自真實經驗的缺乏呢?電影《國寶》將最終上演的劇目改為《鷺娘》,由《阿古屋》的袒護情人,到求之不得的精魂,視覺效果絕美、哀戚,同時呈現出吉澤亮的容顏、身段與演技,是非常成功的策略。日本傳統藝能劇目裡,雪地永遠是充滿情緒張力的舞台。《忠臣藏》的高潮就發生在雪夜——隱姓埋名多年,只為等待時機為主公報仇的浪人武士,在大雪中離開妻兒懷抱,與同志會合後走上殺敵與受罰的不歸路。同樣的,《鷺娘》如果不是在雪夜中起舞,那隨時都會毀滅的堅貞身姿,脆弱與絕美的動人力道必然大減。不過,南國台灣難道沒有堅貞決絕、死而後已的人情故事嗎?日台歷史脈絡中的事件,是不是也能在加害/被害者不在的暗語交換過程中,化為公園榕樹下的精魂呢?
註
㊀ 本文引用版本:《路》(2013年9月,聯經出版)。
㊁ 本文引用版本:《惡人》(2007,中譯本麥田出版,2008)。
㊂ 本文引用版本:《國寶》(中譯本新經典文化出版,2025)。
㊃ 本文引用版本:《橫道世之介》(中譯本新經典文化出版,2020)。
撰文|張文薰
彰化員林人。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現任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研究日治時期台灣小說、東亞文化交涉;主要以比較文學、空間論述為方法框架,關注東亞文化交涉、文學學科體制建構與創作意識等主題。從事日本近現代文學譯介工作,熱愛夏目漱石、谷崎潤一郎的文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