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討愛與金錢、毀滅與重生的複雜關係。潘心彤和富二代辛毅夫挑戰世俗,以「勇敢」作為愛的賭注。周曉琪與精神科醫師顧厚澤則在慾望與欺騙中尋找救贖。面對社會壓力與舊有創傷,他們在權力遊戲中掙扎求存質問:在這浮華世界,愛是否只是自我滿足的自私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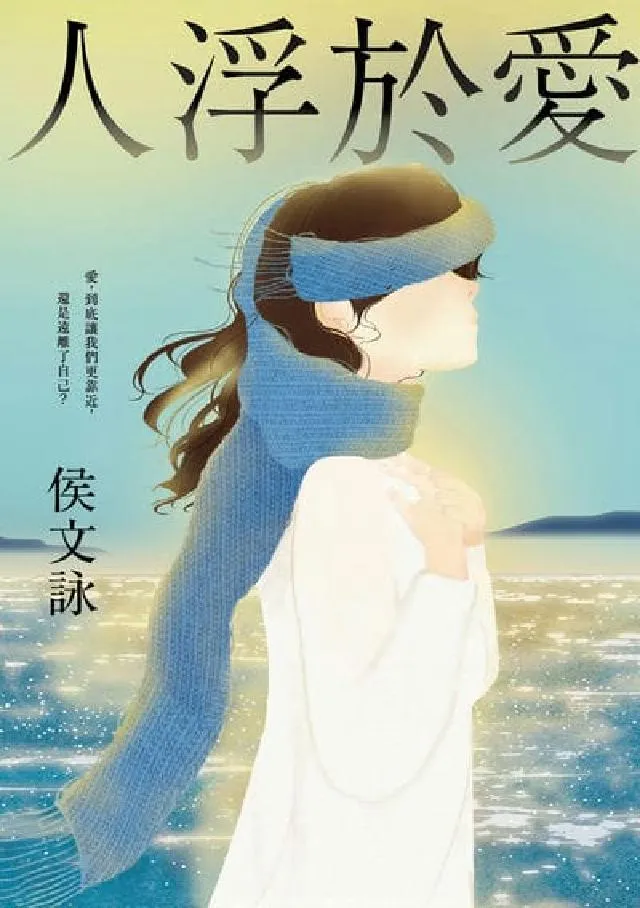
人浮於愛【完全改寫版】
皇冠出版(2025.09)
深入探討愛與金錢、毀滅與重生的複雜關係。潘心彤和富二代辛毅夫挑戰世俗,以「勇敢」作為愛的賭注。周曉琪與精神科醫師顧厚澤則在慾望與欺騙中尋找救贖。面對社會壓力與舊有創傷,他們在權力遊戲中掙扎求存質問:在這浮華世界,愛是否只是自我滿足的自私行為?
Q 這次閱讀過新版《人浮於愛》,發現有不少的調度差異,變成了海明威式的長對白對話,幾乎是重寫了整本小說,這讓我想到諾貝爾獎得主卡爾特斯(Imre Kertész)曾經也大幅度修改小說,甚至重寫。為什麼會進行大篇幅的修改呢?
A 這本書出版已經八年了,這幾年除了寫《變成自己想望的大人》之外,我一直在修改、重寫這本小說,不只是改成目前的新版本,我同時也寫劇本,劇本大概改了十六個版本左右,這樣一來一往幾乎是百萬字;劇本的部分因為遇到疫情,後來又有新團隊加入,我心裡不斷想著,這本小說還可以更好,又改了兩次左右。
我後來在想,會進行大幅度的修改,也許出自於外在環境與內在心態的改變。以前還在求偶階段的時候,不外乎是想找匹配的對象談戀愛,戀愛成功後結婚生子;愛情的公式等於浪漫+性愛+結婚生子+家庭。但到了我的小孩這代,大家不再想結婚了。衛服部調查統計,二十五歲以上的女性有百分之六十七不想結婚,想要有固定伴侶的甚至是兩、三成——戀愛的定義在這十年有了劇烈的變化。
一、兩百年來,我們看到的愛情都是瓊瑤、望春風等以「相思」為主題的愛情,李白或李清照也都是閨怨相思,但到了現在,愛情的定義被推翻了——這是一個超級特殊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愛情小說,沒有過往認知的浪漫,更多的是其中破碎的心靈,以及渴望但不可得的狀態。
人類是一個矛盾的動物。過去我在寫《白色巨塔》時,寫醫療體系下的人們,但延伸出去談權力的爭奪;《危險心靈》寫教育,大家理應分享知識的喜悅,但全都是殘酷的競爭。以上這兩點在這幾十年間都沒有改變,所以我不打算去重寫——人類想像之中的優秀文明,最終都會被人類的心靈及其創造的結構所扭曲。我後來意識到,自己以前都在寫外在的組織跟社會,但愛情這個主題非常有趣,因為愛情對抗的總是我們自己;人類靠著關係活著,在裡頭各取所需,當我們稱某段關係為「愛」的時候,因為渴望,就不會計較付出,但會自我懷疑:我們會不會在關係中失去了我們自己?這樣的內在心態,很值得我們用角色的相遇來思索。


Q 在寫這本小說之前,您的前三部長篇小說主角多為男性,《人浮於愛》是首次以兩位出身平凡卻勇敢堅強的女性(心彤、小琪)為主要角色。在創作過程中,您如何研究或模擬這些您生命經驗中沒有的女性內心戲和經驗?對您來說,寫小說是設計角色或遇見角色?
A 我寫長篇小說都會有一個主題——這次是談「愛」。我覺得讓女性來擔綱主要角色會比較有趣,因為女性面對了許多問題,例如懷孕生子,甚至在傳統社會中,教養小孩的也是女性。對女性來說,她必然會身處於愛的前線。
人跟人之間真正的距離並不是性別,因為性別的取樣始終存在於生活,我們周遭有媽媽、姊妹、同學、老師,這看似平常,但仔細一想,這之間肯定有我們看不見的的權力關係。我在寫小說的過程中,不斷跟周遭的女性討論、嘗試理解,也當作一種訓練——小說家是不應該有性別的。
至於角色,當年《危險心靈》的謝政傑是有完整原型的。有了一群原型,就有大概的角色模板與故事結構,就可以增添細節。但如果沒有原型,要去設計一個不存在的人,不管再怎麼寫都會很彆扭。這次三個女主角雖然沒有完整的原型,但我都「交手」過,體驗過這些人的特質,並且曾好好相處。例如范月姣是我從精神科的經驗、我與粉絲溝通的經驗,以及周遭人的經驗來切入,我傾聽他們的苦楚,發現她們內心的矛盾,並且重新梳理。
同樣,在寫劇本的時候,我發現自己需要設計出更強烈的情緒,讓讀者能沉浸到劇情之中。寫劇本的經驗也稍許影響到我修改這本小說,當初寫舊版的時候,我很著迷於史蒂芬金、契科夫、毛姆,這些作家的情節很緊湊,甚至連《戰爭與和平》每一章都有「鉤子(hook)」。但這次的新版,我想將鉤子減少,讓人物情感更豐富,讀者才更能體會這個角色經歷了什麼。
這也跟上一題有關,海明威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他設計的長對白很多時候是給對白專注的力量,讓讀者能沉浸其中,同一段文字,不同讀者讀到、感受到的內容不同,這也顯現出讀者各自對該角色著迷程度的差異。角色是作者與讀者一起創造的,作者不擁有全部的解釋權——寫散文的時候可能需要解釋,但小說更需要與讀者一起沉浸。

Q 《沒有神的所在:侯文詠帶你閱讀金瓶梅》中有提到,體悟到慾望才是人情倫理底層的真實。在《人浮於愛》中,您也描寫了股票內線炒股、恐怖情人、計劃殺人等社會案件,甚至設計了涉及醫學倫理的精神科醫師角色。您認為在社會寫實的創作之中,如何界定「人的真實」?
A 倘若我們認真投入《金瓶梅》的文本,我們會發現每一句話都有細節——世界不只吃吃喝喝,裡面都有陰險與貪婪的隱喻。文學不只是故事,它留下了空間,讓人讀到自己,或是在人生歷練之後,發現文學中的某段細節原來應證了某段經驗,自己正在發生從前就知道的事。
我的寫作態度比較像我的醫學背景——醫學之所以成立,是因為誠實。醫生只述說真實與客觀,不能在別人的病歷上寫「病人的血壓可喜可賀」也不會說治好與否,而是在某個範圍之內,解釋藥效、副作用或治療效果,不會太過浪漫或悲觀。我寫作的時候比較是一個觀察者,去寫我看到的人,我想寫的不是社會的寫實,而是人的真實與個體發生過的細節,然後藉由書寫去改觀,去翻轉我們僵化的觀念,例如醫療或教育等等。
寫文學的人,多少可以幫助社會去理解這些事情。隨著文學和文化的進展,作家常是社會進步的小推手——暢銷作家的使命,就是讓大家認識「個體細節」,例如莎士比亞常在作品中嘲弄天主教,因為他支持新教,而百年後的英國是以新教為主,他的寫作呼應了文明的寫實,讓我們看到了歷史的過程。這就像《危險心靈》寫大抗爭,過了幾年,剛好發生太陽花運動,有些讀者說我會預言,其實不是,而是文學寫作本來就是一個判斷、推測時代氛圍與走向的方式——所謂「人的寫實」,就是他的內心世界想要變成某個預設的模樣。無奈,社會沒有太大的溝通空間,報紙或媒體上的爭論很快就消失了,我們預想的模樣終究會落敗,只能將想法寄望於過去和未來。這就是戲劇或小說存在的功效:一個文本對社會的幫忙遠超我們的想像,它收留了許多我們在平常體驗到但沒意識到的事,然後在我們最迫切的時刻將它重新喚起。

Q 小說中許多角色都在追尋「愛」的真諦。范月姣認為愛是「為一個比自己更重要的目標活著或死去」,老教授則稱愛「更接近信仰,是給予而非得到」。范月姣、顧厚澤、周曉琪三人間「有病的愛」是全書中很值得玩味的一種情感關係,為什麼會想設計出挑戰倫理跟精神疾病的虐戀?是想反映出什麼愛的觀念呢?
A 小說中有五個主要角色,兩條對照的愛情線。我寫潘心彤的時候比較痛苦,她看起來就是遇到富二代的小資女孩,但如果沒有這條「物質世界」的線,我就沒辦法寫出另一條不追求更好的生活、只是互相補足心靈空洞的三角關係。三個人互相補洞,所以彼此依靠在一起;也因為補洞,彼此爭奪。這兩條線交織在一起,物質世界與內心世界,一條冷,一條熱;在故事的最後,一方獲得了愛與金錢,但反而失去了所有,懷疑這是否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另一方失去了愛,卻在最後想通,發現自己擁有很多,並安慰自己:我的人生該有的都有了。我們的人生到最後都是死路一條,完全無法預知自己的得失,大家都在愛裡頭浮浮沉沉,去學習如何轉念、如何找到說服自己的方法——畢竟,幸福就是說服自己,但自己也是最不容易說服的。
採訪撰文|曹馭博
一九九四年生,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新詩首獎,臺灣文學金典獎蓓蕾獎,Openbook年度好書獎,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出版詩集《我害怕屋瓦》,《夜的大赦》,短篇小說《愛是失守的煞車》。
攝影|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