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欽在紀錄片《大海浮夢》裡,藏了一份祕密禮物要送給夏曼.藍波安。行前收到提醒,請勿爆雷。一時之間,竟不知該如何提問。只能從頭問起。擅長拍海的紀錄片導演,與擅長寫海的作家,最好的相識地當然也在海洋。二〇一九年夏天,周文欽和朋友在龜山島,法文譯者吳坤墉突然說要帶一個朋友來跟大家認識,那個人就是夏曼.藍波安。
夏曼·藍波安
Syaman Rapongan,達悟族人,一九五七年生於蘭嶼。一九九〇年代,陸續出版神話集《八代灣的神話故事》、散文集《冷海情深》、長篇小說《黑色的翅膀》,正式踏上文學之路,獲獎無數,奠定其作為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中獨樹一格的海洋文學作家的重要地位。
周文欽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研究所。他擅長運用鏡頭語言刻畫人物特色及情感,尤以海洋及人物題材見長。從鏡頭到導筒,他擁有逾二十年的豐富經驗,深入涉獵影像製作環節,致力於創作具深度與影響力的紀錄片。
Soulmate POP QUIZ ↘
Q 請和我們分享印象最深刻的夢?

夏曼·藍波安:小時候玩累了,在哨亭夢到去了南太平洋。四十八歲那年,我把夢實現了。
周文欽:童年常夢到在冬山河下游玩水,海底躍出鯨魚,飛過我的頭頂。
Q 提及海洋,最先想到或最喜歡的藝術作品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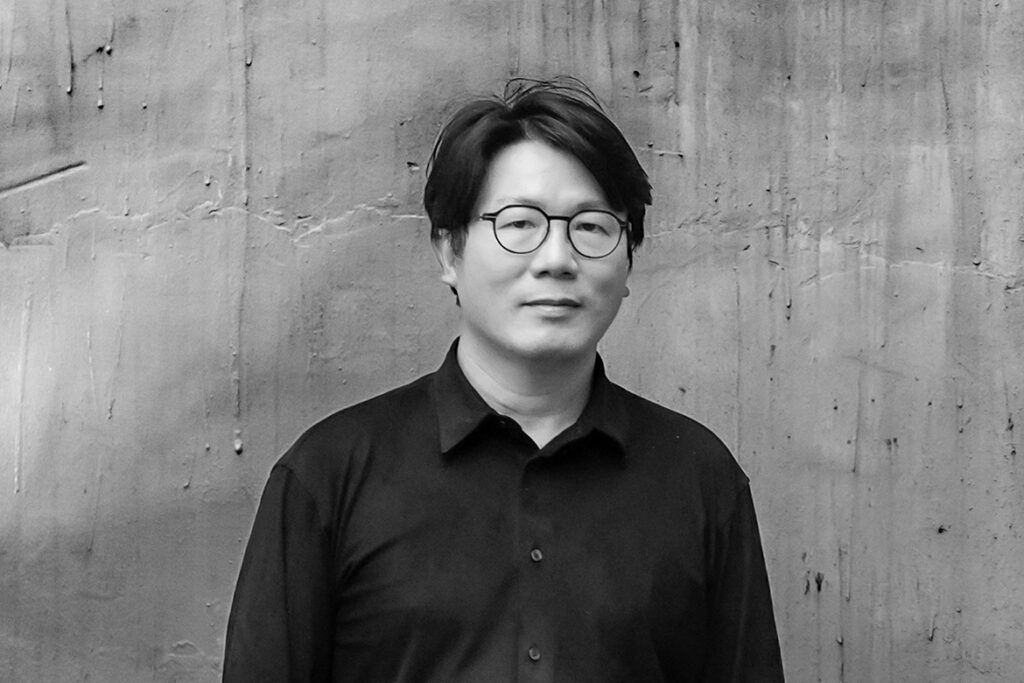
周文欽:日本藝術家杉本博司,他拍的海非常令人著迷。

夏曼·藍波安:法國文學家畢爾.羅逖的《冰島漁夫》。海洋小說一定要談到愛情嗎?
Q 最喜歡海洋的什麼特質?

夏曼·藍波安:我喜歡秋冬兩季的蘭嶼,遊客走了,島很輕盈。
周文欽:變幻莫測。洶湧或平靜都變化快速。
Q 若能交換彼此靈魂的一部分,最想擁有對方哪一項能力或特質?

周文欽:創作力,能以創作表現出自己的心情。
夏曼·藍波安:傻傻的人,每次來蘭嶼都搬很多器材。那種至少有所準備的謹慎。
回憶起相識那天,周文欽說:「那一天,大家都很輕鬆自在,老師拿了朋友的魚槍下去打魚。我剛好手邊有器材,就幫他拍,剪了一支短短的影片送給他。他看了以後跟我說,有個計畫放在心裡好幾年了,想要去執行……」同年九月,周文欽就跟著夏曼.藍波安走進了蘭嶼山裡,拍他帶著兒子去鋸樹,「要造他們第一艘親子舟。」
半年之後,逐漸感受到作家有其獨特的生命史觀,伴隨難解的糾結,想用長片將有故事的人拍好。聯絡了目宿媒體,才知道他們的「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一直想拍夏曼.藍波安,正在找合適的團隊,周文欽就出現了。
殊不知接著就是歷經疫情,拍拍停停。甚至有過團隊進入蘭嶼後,忽然收到再過兩、三天要封島的消息,封多久?不知道。紀錄片裡的拼板舟做了五百多天,周文欽也曾一人帶著八件行李,高鐵台鐵計程車,後壁湖住一晚,隔日再搭四個小時的船晃到蘭嶼,「結果因為天氣或心情的關係,老師不下海。」周文欽苦笑表示,都是日常。
就像採訪這天,夏曼.藍波安臨時因身體不適,請人轉達了會晚點到,或者不到。周文欽聽後,也沒有慌張,大概是拍多了海,早懂得海象不可測。我問他,這次拍的海和以往有何不同?他說:「蘭嶼的海不是溫馴的,是很野的。不管是海面或海底,它的洋流是非常強的。」
聽著也像在形容夏曼.藍波安。拍過三十多部和海洋有關的紀錄片,周文欽說自己在宜蘭海邊長大,「小時候很喜歡在夏天的晚上,跑去躺在海灘上看星空,阿兵哥三不五時拿著手電筒、牽著狼犬巡邏。我是生長在這樣環境的人。」
如果說夏曼.藍波安是用書寫在召喚與海洋有關的記憶,周文欽就是用影像在做同樣的事。確實是找不到更適合做這份工作的團隊了。周文欽也一路拍,拍到夏曼.藍波安忍不住如此形容周文欽:「傻傻的一個人,每次來蘭嶼都搬那麼多器材。我看他搬那些儀器就累了……但我找周導拍,也是想趁我還有體力時,要談我的文學。我在蘭嶼島上的日常生活就是我的文學。那個魚就是我的文學,山林生態就是我的文學。」
後來,周文欽便自由地進出於作家的生活。「我也不跟他說我要不要拍,反正他也不理我。有一天我去,發現他沒有在寫作,在睡覺。我就想,來拍他睡覺好了,拍的當下發現他眼球一直在動,正在做夢。」
整部電影的底色,大概也像一個深邃藍色的夢。拍攝工作一路進行,二〇二二、二三年開始剪片,剪了十幾個版本,始終少了點什麼。周文欽說:「很重要的核心命題是,老師為什麼要帶著兒子去造舟?動機是什麼?」

後來周文欽才發現,關鍵是父親。達悟族有「親從子名」的傳統,孩子「藍波安」出生後,「夏曼.藍波安」才出現,意指「藍波安的父親」,而孩子的祖父則成為「夏本.藍波安」。電影中反覆混剪的歷史畫面,則一層層揭開謎底:一切不過是一場朝向故鄉、父輩、血緣的返程。魔幻的是,父子長得太相像了,周文欽總是拍著拍著就開始想,「我到底是在拍藍波安,還是在拍年輕的老師?」
夏曼.藍波安帶著兒子造舟,會不會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回應曾帶他造舟的父親?終於見到面後,他和我們分享生命中極其重要的一次出航,在十六歲,搭船出海,媽媽還喊:「你是男人,可以跳下來游回陸地。」但他還是離開了,「我要改變我的身分階級。可是來台灣唸書,不是那麼容易啊。沒有人會給我明天的錢啊。要去打工,去蓋房子……全部要靠自己,想來想去都會流眼淚。」
那幾年,他最深切的身體感受是「飢餓」,餓到胃潰痬,餓到自己拿墨水刺青,用疼痛忘記飢餓,現在身上還有一個家族的圖騰符號。我們問夏曼.藍波安,三十二歲返鄉,最關鍵的原因是什麼?他說:「我爸爸有一次來看他的孫子,說:『孩子啊,回家吧!』」
他曾在《冷海情深》中如此寫道:「父親問我:『你何時愛上我們的海?』我思考了半晌,我不知道。父親心有難解的沉默神態,說:『從你出生捧在手掌上的那一刻,我就按祖先的習俗,說:『讓我的長子像海那樣堅強』按祖先的習慣,達悟的男人絕對要愛海,和海做朋友……』父親總一句話說:『因為海洋的關係,才有我們這個民族。』」
他回家了。父親等到了他,如今他也等到了兒子。他說:「造舟是達悟人的天職。對我來說,帶兒子去山裡面走那麼多趟,帶他潛水抓魚那麼多趟,都是父親要做的事……」下水儀式那天,父與子兩人在岸邊無語看海,那大概也是一種心有難解的沉默神態。夏曼.藍波安流下了眼淚。
關於那眼淚,周文欽的解讀是,「老師終於做到他父親的期盼,就是帶著孩子造舟。他不是說要帶藍波安上山,是從他出生就已經決定要做的事情?可是這一晃眼已經快三十年了。」
夏曼.藍波安則是說:「有一點感慨……驀然回首,只是為了幾本書,幾張紙,並沒有帶給自己的家庭、小孩,更充裕的生活。我們是很幸福,可是我們是在貧窮裡面過著幸福的日子。」
紀錄片的最後,周文欽用一個長鏡頭收束了這個故事。那是飛魚來的季節前,父子倆每天都出海去捕鬼頭刀,周文欽看見了,在岸上凝視般拍下,廣袤無邊的海上,一葉渺小的舟,慢慢漂流,從左到右。達悟族人對大海的倚賴、敬畏,盡付於一幕之中。父與子,夏曼和夏本,也在那一幕中,完成了傳承。
採訪撰文|湖南蟲
臺北人。樹德科技大學企管系畢業。曾任職出版社、報社,現為自由文字工作者。經營個人新聞台「頹廢的下午」。著有《最靠近黑洞的星星》、《小朋友》、《一起移動》、《水鬼事變》等。
攝影|汪正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