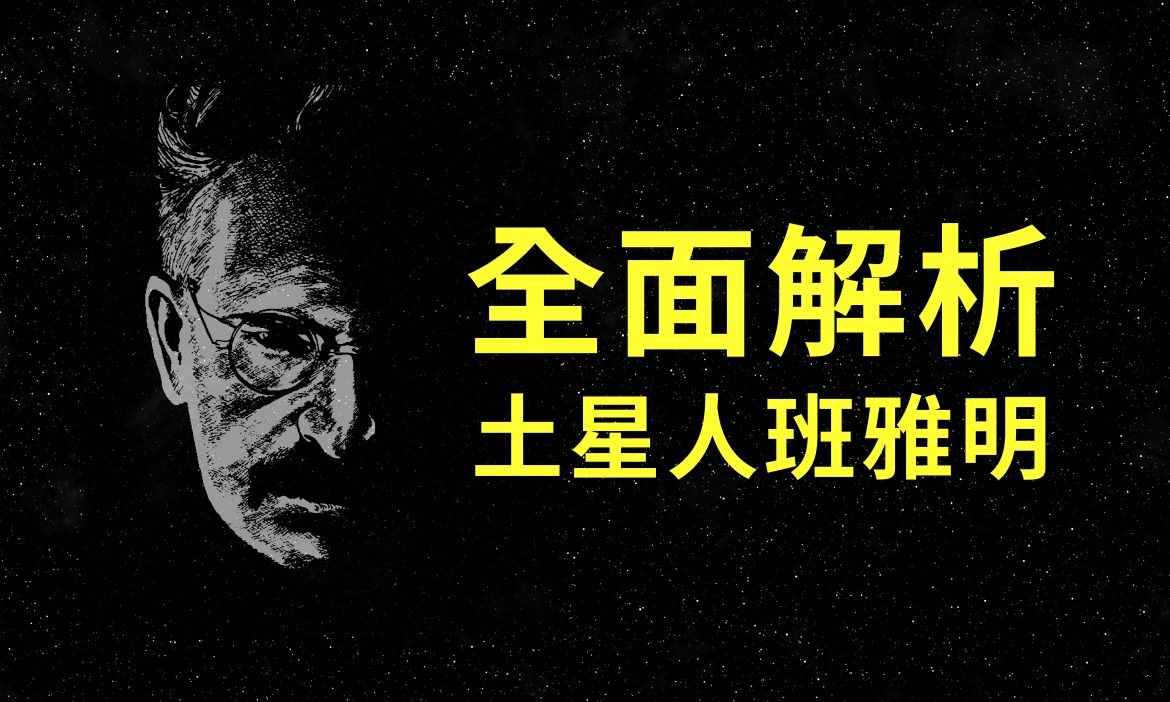如繁星又如璀璨鎏金的班雅明思想,收服諸多二十世紀以降的藝文愛好者。他們琅琅上口的詞語,譬如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的「靈光」,漫遊拱廊街與鬧市的「閒逛者」。這回,讓我們看看四位當代文青怎麼說,由政大哲學系蔡偉鼎老師,引領我們深入思考,如何解讀這四個常見的專有名詞。

余知奇|微光咖啡負責人

箕子|北漂青年(剛分手)現從事服務業

莊崇暉|政大傳播學院畢業

秦政德|小草藝術學院N號志工
答題者|余知奇 微光咖啡負責人
班雅明說真正的藝術品,周遭有著一層微弱的光暈——Aura(靈光)。「微光」則是我對Aura一字的視覺性轉譯。而身為第三波咖啡浪潮在台灣的推廣者,我也用它來描繪精品咖啡。靈光來自於藝術品的獨一無二(unique)——它創造於獨一無二的時空中、它渡過了獨一無二的歷程。於是我們見它的同時,彷彿心領了它親身的故事與價值。班雅明一邊緬懷靈光的消逝,但也樂觀地指出:在機械複製的時代,藝術品將從廟宇或博物館中解放出來,更容易地散播到一般人的生活中。我在精品咖啡上,也彷彿見著了靈光。精品咖啡的核心精神,在於從種植、後製、烘焙到沖煮整個生產環節的精緻化,並強調每一支單品咖啡因來自不同的風土、有著獨特香氣的「地域之味」。如今處在資本商品充斥的社會中,其實我們很難遇見真正獨一無二的「藝術品」。若說班雅明能給我們什麼生活上的啟示,或許在討論生產過程之外,我們可以反向從自身為其創造出獨特的故事(例如贈送者的身份),讓複製品也可以重新擁有微弱的光暈。
班雅明使用「靈光」(Aura)這個術語來指稱某種可在傳統藝術作品上感受到的性質,並認為其在複製技術發達的現代世界裡終將消逝。他這種「靈光消逝」的論點非常吸引人,也頗獲懷舊之人所認同,所以迄今仍不斷被人傳誦。但到底「靈光」是什麼?首先,它並非指特定的藝術表現手法或風格,而是如班雅明在〈論波德萊爾的幾個主題〉(Über einige Motive bei Baudelaire)一文中所言,意指群聚圍繞於某一直觀對象、且定居於非自願記憶(mémoire involontaire)中的諸般表象(Vorstellungen)。既稱之為「表象」,即意味著其有涉入鑑賞者的個人意識;說它「定居於非自願記憶」,則表示其與該對象之外部歷史密切相繫。其次,班雅明曾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以自然世界的直觀對象(遠山或枝頭)為例,描述吾人感受到其靈光時的經驗為「某一遙遠者之一次性的顯現,縱使其可能近在咫尺」。若我們對這個簡短的描述進一步考察,則可發現當一件藝術作品顯現出班雅明所謂的「靈光」時,其理應具有以下四項特徵:❶此時此地性(das Hier und Jetzt),意指其總是處在具體的時空脈絡裡;❷獨一無二性(Einzigkeit),亦即它的每次顯現都是僅此一次的;❸真跡性(Echtheit),此則是要強調該藝術作品係屬原作、而非贗品;以及❹不可逼近性(Unnahbarkeit),這是因為它具有某種崇拜價值、不可褻玩,所以才會讓人感到雖近猶遠。總之,古典藝術的大師作品無疑均能完全滿足上述的四項特徵,至於後世對這些作品的複製則否,故才無法顯現出同樣的靈光來。儘管如此,班雅明認為手工複製跟機械複製仍有差別,因為前者畢竟為手作之物,會在製作過程中偶然夾帶進一些不一樣的元素,以致依舊可能具有某種獨特性,相較之下機械複製的藝術作品則會因其標準化製程而排除掉這些偶然性。這意味著,只要匠人手藝一息尚存,其親手精心複製的作品相較下還會保有相當程度的靈光。就此而言,余知奇的理解很貼切,因為手沖咖啡比起機器沖泡出來的咖啡,確實會閃現出隱隱的靈光,誘惑懷舊的饕客去選用。
答題者|莊崇暉 政大傳播學院畢業
班雅明的閒逛者概念大致上有幾個重要的關鍵字:直覺觀察、城市街道遊蕩、非我族類與視覺消費。詩人波特萊爾眼中,十九世紀的巴黎整體是沉鬱的,在象徵工業奢侈產物的拱廊街裡即可感受。閒逛者則是新舊空間交替、社交方式轉變、櫥窗商品湧現之際,將目光逸散在符號景觀中的人。回到班雅明的語境,閒逛者是矛盾的,不經心地涉入(involvement)又得抽離(detachment)觀看城市邊緣的華麗與破敗。閒逛者也具備抵抗屬性。在變動的城市空間與時間中,能細微感受到「生存」是怎麼一回事。對資本主義、勞動分工、消費文化的對抗則成為閒逛者得以看見異化人群、物件本真性的視覺基礎。看看現代,部分借/濫用閒逛者意義的主張認為,社群媒體上幾乎都是「社群閒逛者」,我並不認同。因為閒逛者要有獨到的直覺與觀點,以表現自己的價值。
「閒逛者」(Flaneur)是班雅明的「拱廊街計畫」所要處理的主題之一。「閒逛者」一詞按其字面義,意指那些無計劃地隨走隨看、又樂在其中的人。不過,當班雅明使用該詞來指稱現代社會發展末期的一種生活類型時,他所意指者顯然已超出了其字面義。那麼到底他說的閒逛者是誰呢?這個問題不易回答,因為閒逛者恰恰正是那些無法在資產階級社會裡被清楚定位的人。按照班雅明在〈波德萊爾筆下第二帝國的巴黎〉的描述,「閒逛者」具有以下幾個特徵:❶閒逛者樂於去辨別路人所屬之社會階層、認識更多人性,以利其在險惡的大都市裡求生存;❷閒逛者是一種刻意躲在人群裡的人,只因如此他才不會感到不安;❸閒逛者視空閒為其個性,以抗議現代專業分工社會所標榜的忙碌;❹閒逛者是沉迷在人群中的棄民,儘管其仍如商品一樣待價而沽。班雅明分別以作家、偵探、詩人、妓女等例來闡明這些特徵,而這些人都不能被簡單納入典型的勞動關係中。由此推知,班雅明所謂的「閒逛者」,簡單來說,就是那些不被資本主義社會的邏輯所收編、但又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人。就此而言,莊崇暉的理解是有精確看出「Flaneur」那在現代主義資本社會中既涉入又抽離的性格,只不過當其反對將社群媒體使用者稱為「Flaneur」時,毋寧是高估了該詞之義,而更像是用尼采的「Wanderer」(漫遊者)概念來理解它。
答題者|箕子 北漂青年(剛分手)現從事服務業
政治就是眾人之事,藝術當然也不例外。班雅明提出「靈光」的概念,批評了複製技術的出現,讓藝術品失去了原先獨一無二的時空背景、「靈光」消逝。繼續延伸下去,複製的藝術品將發揮什麼樣的功能?甚至它存在的目的是什麼?在那個法西斯主義高張、對個人偶像崇拜與神話充斥的時代氛圍,複製的藝術品與政治神話產生連結,鼓吹其大量生產、製造,讓政治顯得「美麗高雅」。如此,能讓大眾深陷其中而不自覺,並激發狂熱,讓獨裁者有能力掌控全局。
在康德提出「美是不帶任何旨趣的愉悅感」這個論點後,西方逐漸流行一種美學觀,認為藝術本身即具有某種內在的價值,不應受到任何外在目的與旨趣所決定,並且自十九世紀下半葉起多以「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這個口號來自我標榜。依循該口號的邏輯來看,藝術活動在本質上不但以自身為目的,更還具有某種神聖般的純潔性,以致於其只要被牽連到任何外在的利益關係時,都彷彿是玷污了它。而這種美學觀迄今依舊盛行於世,譬如:每當有藝術家或藝術作品因為特殊的政治因素而無法表演或展出時,吾人總是不時聽到世人嚷嚷著說「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彷彿這兩者本來就不該混為一談。然而,班雅明卻反對此看法。他清楚地洞察到「美學」與「政治」這兩個領域絕非是毫無關聯的——縱使是那些「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作品,仍舊是某一特定社會結構下的產物,因而總是隱隱地在為某一特定社會階層服務。由此可見,班雅明的美學觀基本上仍是基於一套唯物史觀,認為文化藝術之意識形態係奠基於經濟技術等物質層面上,也隨之而變。此外,班雅明雖沒有明確提出「政治美學」一詞,但他確實可視為政治美學理論的先驅。按其看法,政治美學包含兩個部分,亦即政治的美學化(Ästhetisierung der Politik)和美學的政治化(Politisierung der Ästhetik):前者暗指的是納粹政權(作為極右派的資產階級政黨)為了美化自身意識形態所採用的藝術表現手法,以營造與維護政治人物的光環;後者則是指無產階級通過機械複製技術來削弱藝術作品之靈光,以翻轉資產階級的美學觀。班雅明的主張是,吾人應以美學的政治化來對抗政治的美學化。就此而言,箕子雖看到藝術與政治並非不相干,但其推論卻相反於班雅明,因為後者恰恰是要透過大量複製的通俗藝術品來顛覆法西斯政權所推崇的高雅藝術品。
答題者|秦政德 小草藝術學院N號志工
總是於複雜迷宮裡百轉千折、不停迂迴試探的創作歷程,是不是也像在地圖未曾標記的全然空白邊境,以肉身與靈魂地冒險衝撞,企求刻繪出一道可能逃逸域外的突穿縫徑呢?創作之所以誘人前仆後繼,對於絕大多數奮不顧身投入的創作者而言,共同之密語或許是因為鋪展、延伸在彼此眼前的正是條——雖如同深沉黑洞似只噬不出、僅供單向通行,卻又更像是數不清有多少未知星系閃亮運行的銀河廊街。
這個問題可先從班雅明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單行道》(Einbahnstraße)一書談起。他這本書總共收錄了六十篇長短不一的雜文,分別就所觀察的諸般不同人、事、物加以評述。乍見之下,書中各篇文章的標題令人眼花撩亂而毫無共通之處,所談論的對象彼此間亦無什麼密切關聯性。更令人費解的是,班雅明逕選了「單行道」這個名詞來當作匯輯這些雜文而成的書籍之書名,書名與諸篇名間更是狀似八竿子打不著,實在讓人看不出其用意到底何在。唯一可供讀者揣測的線索則是:他在書中扉頁裡將這條「單行道」命名為「阿希雅.拉齊絲路」(Asja-Lacis-Strasse),而其理由是這條路乃是作為工程師的拉齊絲在作者內心裡所開鑿出來的。進一步參照班雅明的傳記,則可知拉齊絲是班雅明在一九二四年於意大利卡布里島所愛上的一位拉脫維亞裔女演員暨劇場導演,並且也是班雅明的左派意識啟蒙者。光憑此點來推想,那麼《單行道》大約就是班雅明隨筆寄情於物的愛情小品文集罷了。不過,此事並不簡單。阿多諾曾評論過此書,稱它是班雅明研究現代主義起源的第一部作品,換言之,亦即是其「拱廊街計畫」(Das Passagen-Werk)的首作——這意味著,班雅明在《單行道》裡所談論的紛雜對象,毋寧都是放在現代主義的脈絡下來理解的。此外,阿多諾還提示班雅明在《單行道》中是通過「思想圖像」(Denkbild)這種突破概念思維僵化框架的表達方式來捕捉現代社會發展下的諸般面貌,尤其是那些被現代概念思維所輕視、遺漏掉的面向。這說明了為何《單行道》一書不是採取學院派所熟悉的論證風格來撰寫。最後,阿多諾指出班雅明在《單行道》裡旨在揭示出其所預感到的現代主義之衰亡趨勢,而這點說明了為何班雅明要以「單行道」作為書名,因為「單行道」是一種規範一切交通工具只能朝單一方向前進的道路,而現代主義的發展對他來說正如同單行道一樣,一旦車子開了進去,就算是開車的人看到前方路況不對勁而想要掉頭走回,後面蜂擁而上的車子仍會推著它向前走,直到一起步入毀滅為止。就此而言,秦政德的理解毋寧是僅以浪漫主義式的思維來詮釋「單行道」,而忽略了班雅明其中對現代主義的批判。
解析|蔡偉鼎
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詮釋學、語言哲學、藝術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