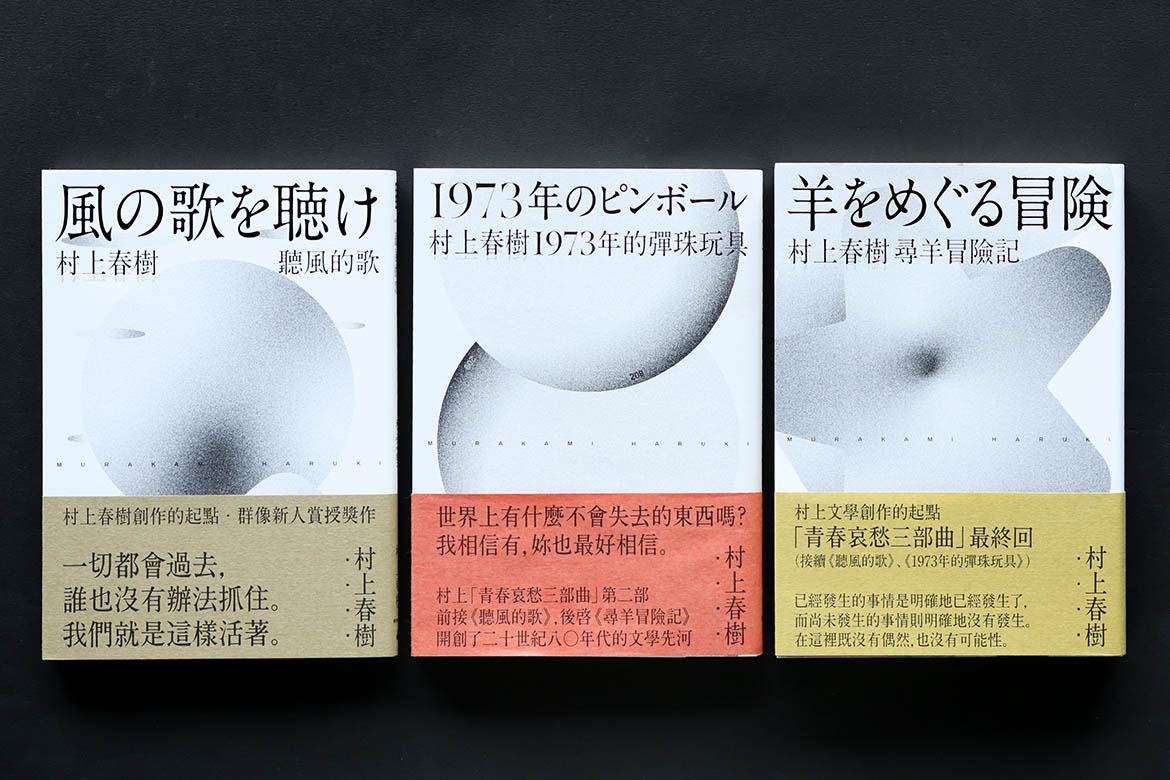三十歲前,我很幸運地擁有過兩次「村上的初體驗」──第一次是為了排解車禍現場般,早已亡故的愛情關係,而去讀紅色書封版的《挪威的森林》,那一年我是「直子」派;第二次初體驗,則是身分更易,變成村上台灣新書的工作人員──當時我只是小小的兼職行銷。那年《村上T》準備出版,我捧著沉甸甸一疊紙稿,寄給作家們讀,並且神聖、虔誠地,去擬一些關於邀約的信。身邊的朋友聊起村上,或多或少都能談起一點他的某本書。說起來,每個文學愛好者應該都能談出一段屬於自己的「村上時間」。
青春與哀愁三部曲我反而很慢才補齊。閱讀時,經常感覺過往的自己被召喚回來。青春的其中一種特性,是肉體能夠隨著時間,明確感覺到它的消失與結束。無論用什麼方法,都會在某一年離開人的身體,使人瞬間明白:「我好像不能再用以前那樣的想法生活下去了。這樣子好像是行不通的。」
在青春尚未徹底退場、人也還沒完全成熟的曖昧之地,村上運用小說無限開展了這個空間:在這系列中我們可以看到眾多角色懸空於哀勉的情結中,但讀者未必知道這種愁緒所為何來。他們少數能夠被明確指認出來的舉止,就是時常感嘆日復一日消逝且無聊的時間,以及談及自己漸趨壞老的身體。
「所謂軟弱是身體裡面逐漸腐敗的東西。簡直就像爛瘡一樣。我從十五歲前後開始一直繼續有那種感覺。自己體內確實有什麼在腐敗當中…….你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嗎?」──《尋羊冒險記》。
青春是活生生,像生命一樣會「湮滅」的東西。只是沒人知道:它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會離開。「我」跟老鼠從《聽風的歌》、《1973年的彈珠玩具》到《尋羊冒險記》,不斷地推遲這場「湮滅」的發生。尋找彈珠檯,跟找到背後有星的羊到底代表什麼?或許這件事的答案,反而是最不重要的事。重點在於他們(我們)往往在生命中,因各種因素必須啟程、必須生活、必須與「二十代」的自己告別。這種對自身生命階段的敏感、周圍社會環境巨變的無能為力,是幾乎所有人多少都曾經歷過的,青春的碎片。(如同三一八學運之於我輩,也有層次不同的影響。)
這三部曲也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寫這些「個體」前所未有的孤獨。這種孤獨,可以視作群體生活對這些人太過灼熱而燙傷的逃逸之路。譬如《聽風的歌》、《1973年的彈珠玩具》在在提到的大學生活(老鼠即是因此大三輟學)、「學潮」等,老鼠甚至厭棄閱讀任何一本書。在一篇與譯者洪金珠的對談中,村上春樹談到自己對學運的經驗:
當年搞學運的人很多,我不過其中的一員罷了。學運對於我的小說並沒有什麼影響,那次的學運倒是讓我「對於文字失去信賴」;例如,有一個字眼叫做「革命」,當時我們一聽到這個字眼就心跳加速,興奮得不得了,覺得這個字眼非常正確、有正義。但事情過去後才發現「革命」不過是個「語彙」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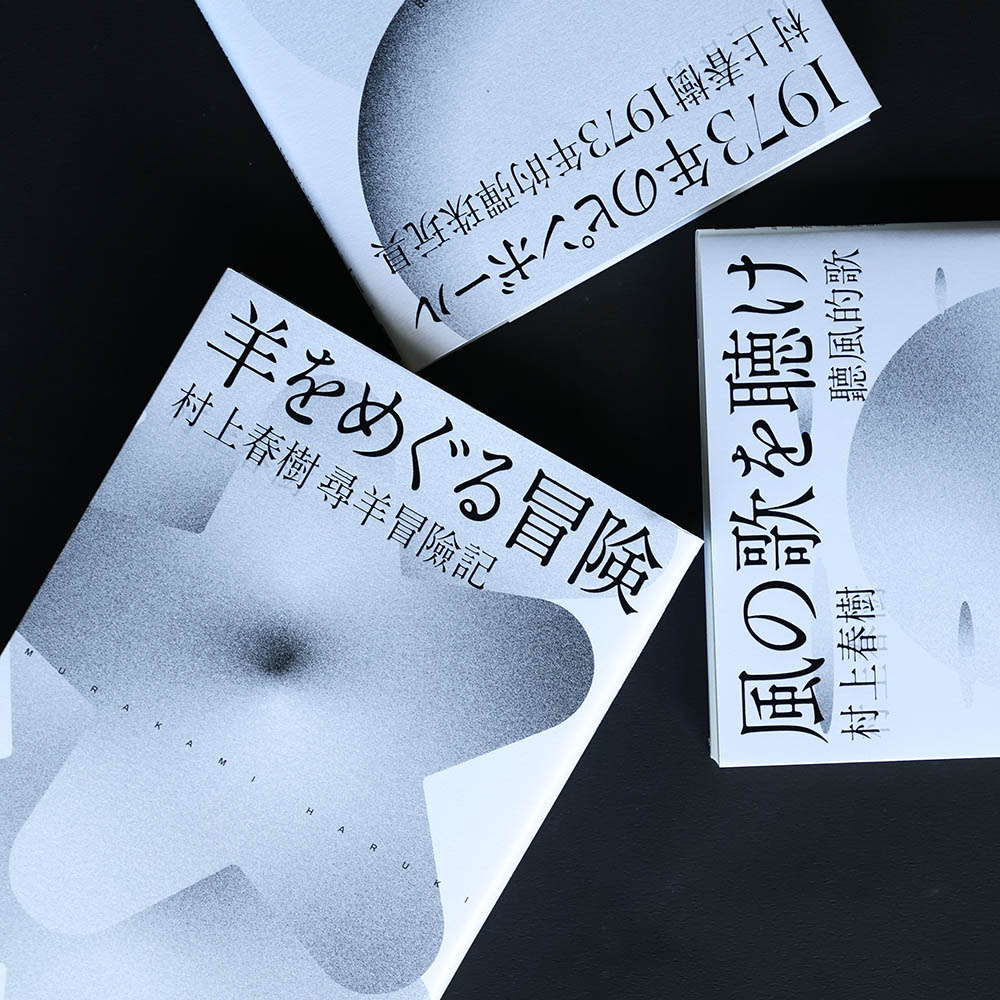
這篇訪談或許可以稍微解釋到,為何村上早年數本小說喜歡提及學運,讓角色與運動的關係互為表裡,又有點隔閡。有趣的是,《尋羊冒險記》是歷史元素最豐厚的一本作品,本書利用星羊的譬喻、十二瀧町與戰爭的歷史,逼迫「我」踏上了他根本無法解決的巨大旅途。我個人非常訝異也格外欣賞的設計,是老鼠在《尋羊冒險記》中,正式揭露了他隱藏的過去,成為某段歷史的餘緒(即便他本人極度想脫離這些標籤)。為了了斷這一切,老鼠趁「星羊」奪舍自己肉身時露出的短暫空隙自盡,並且請「我」臨走前接上預留的炸彈,將先生的秘書炸死。讓「我」在形而上的意義上,澈底終結老鼠痛苦、靈肉分離的一生。
如要用隱喻的角度來剖析這段重要的結局,其中一種解釋,是人必須以某種近乎暴力的形式,送葬自己偏執的單純。「我」早早預料到這場生命的爆炸,從此不得不提早傷感。早慧者或許都有類似的經驗:首先是無以名狀的孤獨,然後發現是自己總是活在不合時宜的空間,最後才意識到:一直這樣思考的日子總有一天要結束的。一旦結束便意味青春的終結。人會親自抹掉曾堅信的物事,作為獻祭給自己的「成年禮」。
爾後會怎麼樣?沒人知道。而旅途還沒結束。時間是無可退換的單程票,不知道自己會在哪一站下車。多年後,村上春樹預言似的,在《尋羊冒險記》續作《舞.舞.舞》中寫下一句:「大家就算不願意也會變成大人。」
撰文|趙鴻祐
一九九四年生,新北人,東海中文所碩士,現職行銷企畫。著有短篇小說集《烏鴉與猛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