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臺灣到德國,從歷史到日常,我們邀請長年定居臺灣的德國小說家施益堅,與曾旅居德國的臺灣作家吳億偉,展開一場跨文化的對談。他們交換各自的異地生活經驗,談語言的陌生與熟悉、文化記憶的斷裂與縫合,也談在不同語境中成為寫作者的可能與侷限。兩人以書寫為出發點,讓「異鄉」不只是地理位置的轉換,更是一場持續進行的思維轉向與身份探問。

施益堅
1972年出生於德國的比登科普夫,主修哲學、宗教學以及漢學,在東亞生活與工作了15年。曾先後到中國、日本、臺灣等地做研究和居留,觀察每一座城市的風土人情。而在臺灣居住的時間最長,同時完成第一部小說《邊境行走》,注定與臺灣讀者締結最深刻的緣分。曾任德國國家研究機構學者、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國立中興大學駐校作家。出版小說《邊境行走》、《離心旋轉》、《對手戲》等,另著有台灣通史《台灣使用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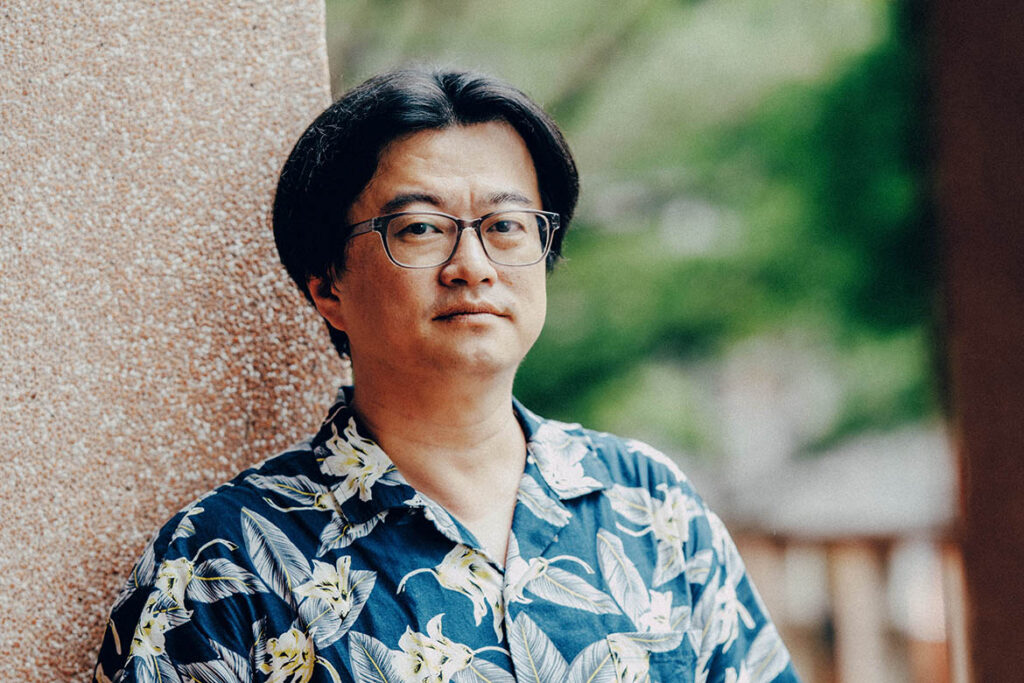
吳億偉
德國海德堡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暨漢學系博士。曾為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博士培育人員,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亞洲研究所訪問學者,並於清華大學中文系與寫作中心開設文學創作課程。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時報開卷好書獎,入圍金鼎獎與台灣文學金典獎,連續兩年入圍臺北國際書展書展大獎決選。出版短篇小說集《芭樂人生》、散文集《努力工作:我的家族勞動紀事》、《機車生活》等。
Q 請問兩位最初如何開啟「德國到臺灣」與「臺灣到德國」的生活?
施益堅(後簡稱施) 我1996年初次來臺灣,馬上覺得跟中國不一樣。在臺灣,晚上可以跟朋友去酒吧,電影院有西方電影,也有英文報紙;生活很像西方人,氣氛也蠻自由。但同時,臺灣又能看到餐廳有神位跟很多傳統寺廟,在中國看不到真正古老的東西。我覺得很有趣,想要進一步了解,所以之後又申請來臺灣,在師大繼續學中文。
吳億偉(後簡稱吳) 我是2008年到2014年去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唸書,研究晚清民初報紙上的諷刺畫。這是一段沒想過的人生際遇,當兵那年想出國唸書,剛好海德堡大學成立了歐亞跨文化研究所,有個團隊專門研究亞洲諷刺畫,這延續了我碩士研究,在過程裡更發現晚清民初中國諷刺視覺文化受歐美影響很多,許多諷刺畫是外國圖像的轉譯。我們團隊要研究的,就是隱藏其中種種跨文化模式。今天跟施老師對談,我覺得有種時間的差異,施老師的臺灣仍是現在式,但我所談的德國生活已經是過去式了。

Q 請問兩位在異地生活的外語環境與生活經驗裡,是否遇到哪些困難或難忘的事?
施 我剛來臺灣的時候,網路還沒發展,跟德國的朋友幾乎斷了一年聯繫,只偶爾跟家人講電話。一開始很不容易,但那是很有價值的經驗,逼我踏入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吳 我的博士課程是國際學程,主要交流用英文,不學德語也能取得學位,但我覺得既然到了當地,就要學習當地語言。我很幸運一開始就與一個德國家庭同住,房東太太一家人很有耐心教我德語,帶我融入德國日常。在德國時我常用三種語言,生活德語、工作英語,中文是研究材料。因為使用目的不同,我對這些語言的感受也很不同,德語親切,因為生活感,英語嚴肅,因為學術,然而中文,因為是母語,則給我一種時空錯亂感。那時常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圖書館裡查閱晚清民初的報紙,同份報紙我可能在臺灣、上海、北京也讀過,但一抬頭,四周環境轉換成歐洲房舍街道,彷彿從歷史裡抬頭,現實則不停變換,很有趣。
施 當初去中國只學過一個月中文,感覺突然變成盲人,看得到字但不識字,菜單都看不懂,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來臺灣的時候,已經學了一年中文,生活模式也比較適應;生活很舒服,有自由自在的感覺,後來慢慢發現到社會的多元性。中文進步之後,我走在臺北突然聽到很多種方言,才發現這些人來自中國各個地方,這就是臺灣的複雜性;需要調整我的角度和聽覺,才能探索這個地方。
吳 你在臺灣住那麼久,還有哪件事不太適應的?
施 有件事不是討厭,但覺得有點好笑。我常常聽臺灣人在講這個或那個好吃;這麼重視吃的,我覺得蠻可愛。很多人知道你住臺灣很久,還是會問:「那臺灣料理你吃得習慣嗎?」
吳 德國以麵包爲主食,我最初很不適應;可是離開前,我已能三明治當一餐,不知不覺適應了。回到語言,我剛到德國也聽不懂,可是聽懂之後,又懷念聽不懂的時候;好像整個世界只剩下聲音,你不會被干擾,這是一種出國後才有的感受。出國前,你覺得語言是你的專長,可到另一個世界的時候,才發現你會的都沒有用,這才發現到語言的侷限。房東教我德語時,我學習聆聽那些聲音,讓語言回到最簡單的聲音,對語言有不同感受。我們使用母語時,由於太過熟練,難免用語言包裝語言,但當你得放下這些表面時,就會回歸到說話本身。


我走在臺北突然聽到很多種方言,才發現這些人來自中國各個地方,這就是臺灣的複雜性;需要調整我的角度和聽覺,才能探索這個地方。
Q 在臺/德哪些地方居住最久,最有情感記憶?在異地寫作生活或身為作家的感受是什麼?
施 太太是臺北人,所以我們都住臺北。大概除了中央山脈,所有的城市我都去過;臺灣沒有很大,但有某種歸屬感。我喜歡花東,生活的速度比較慢;也喜歡臺南,南部的天氣好很多,臺北冬天其實蠻難過的。我住屋頂加蓋的房子,因為不喜歡樓上有人;最好我獨自在家,我寫作需要安靜,隔離外在世界,才能完全專心地想像。
吳 你寫完一本書之後,會需要回德國recharge(充電)之類的?
施 不會,我現在已經養成一種節奏,一部作品還沒寫完就會構思下一部;如果需要recharge(充電),旅遊兩三個禮拜就行,我已經習慣這個行業。
吳 作家在德國跟在臺灣受到的社會關注,你覺得差別大嗎?
施 在臺灣說我是作家,很多人會問:「那你的工作是什麼?」因爲他們不相信寫小說有薪水可以生活;在德國,作家蠻被人承認的。德國對文人有些浪漫的想像,文化傳統對作家有某種尊重。
吳 在臺灣,作家容易被認為不是份「正式」或是「安心」的工作,想寫作似乎得先成為什麼才行。比如我自己,到德國雖是機緣,但出國唸書,無非也想找份大學教職,有穩定的收入,才敢放心,或說不讓他人擔心的寫。

德國對文人有些浪漫的想像,文化傳統對作家有某種尊重。
Q 臺灣與德國都有一些曲折的歷史,兩位如何從自身的文化去思考?
施 德國跟臺灣比較相似的是,我們在近代史有很多轉折。我的祖父1901年出生,經歷過德國帝國、威瑪共和、納粹和戰後四種不同國家體制,但是國家語言都沒有改變。我很好奇,臺灣日治到民國,竟然連語言都改變了。我做《梅雨》背景研究時,在德國找到日治時期出生的臺灣人,他小學一年級老師是日本人,說日語;二年級時外省人還沒來,就找臺灣人教書,是講臺語;到了三年級,大陸老師講中文,所以他經歷過三種不同語言的教育。全世界大概只有臺灣有這樣的經驗。臺灣跟德國的歷史都有比較黑暗的階段,很多臺灣跟德國的民間團體有交流,因爲他們想知道社會應該怎麼面對轉型正義的問題,我覺得這是可以彼此了解的部分。
吳 看到柏林圍牆遺跡時,我震撼蠻大的。有次跟朋友聊到納粹,他很不高興,對他而言,那些過去他知道是錯誤了,但無需特意提起。他的回應讓我驚訝。對你來說,這段歷史是不斷的刺激?還是「過去」了?
施 我從小在家或上課都會講到納粹,所以並不覺得敏感。那個時代的人多數都離世了,但重要的是,要提醒自己這是「發生過」的事。不是爲了造成罪惡感,雖然你戰後出生、沒有參與,但是英國、以色列、波蘭會記得。我覺得必須去面對,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也是值得學習的一段時代。
吳 在柏林參觀「查理檢查哨博物館」時我感觸很深,展覽述說了東西德的界線:有些東德的人,躲在船裏越過界線,跑到西德,而小時候我也常聽到「投奔自由」這個詞。幾年前我完成一部中篇小說,還沒出版,就是有關德國、臺灣與「界線」這個主題。臺灣或德國,都有一條戰爭後留下的「線」,我們彷彿都是被界線深深影響的一群人。

臺灣或德國,都有一條戰爭後留下的「線」,我們彷彿都是被界線深深影響的一群人。
Q 跨文化的生命經驗和翻譯是否有影響兩位對文學創作的思考?
施 德文和中文非常不一樣。《梅雨》書名「Pflaumenregen」從中文直譯,是很有魅力的;我如果不會中文,不會想到這個。我用德文寫《梅雨》,但是在我想像裡對話是中文的,因爲我知道他們講中文;所以我先從中文翻譯成德文,然後譯者又把它翻回原文。這比較特別,我尤其會考慮對話,臺灣人會怎麼說,這是很有趣的經驗。我把這部小說當做跨文化的實驗,書裡沒有角色是德國人;但這個跨文化的面向還是存在,我盡量用想像力和經驗接近臺灣人視角。雖然難免會有落差,但我覺得沒關係,因爲歷史小說就是一種詮釋;是我對臺灣歷史社會的詮釋。我的角度也許跟臺灣作家不一樣,但也沒有巨大差異。我最近在柏林參加國際會議,與吳明益同臺;他也說,我是臺灣人,但是太平洋戰爭、日治時期我也沒有體驗,只是有做功課。我對一百年前的德國也很陌生,假如寫德國歷史小說,還是要做很多研究;所以這是相對差異,不是絕對差異。我覺得這是值得進行的實驗;有沒有成功?這不是我可以說的。
吳 到德國唸書,最常被問怎麼會去德國研究中國?我總會解釋,到異地是理解另一個文化的人,怎麼看待自己習以為常的議題,嘗試以多種觀點來分析,讓自己的思維更加多元。在研究與創作之間,做研究是要形成自己的觀點,可以從方法論材料等切入;但創作比較複雜,在於要如何將觀點融入故事中,遇到跨文化的議題時便是挑戰。比如,我小說裡有一個重要角色是德國人,在書寫時,我會思考一個亞洲寫作者如我要如何跨越文化與知識隔閡,到底要採取什麼角度去寫?
施 寫小說是儘量瞭解生活環境,這對我來說就是臺灣。我跟所有作家一樣,把面前的世界當作題材。《梅雨》因爲題材比較邊緣,在德國沒有熱賣;但有興趣的人都很喜歡,臺灣作家的書很少德文版,所以可以透過讀這本小說來認識臺灣。

採訪撰文|李筱涵
學者、作家,臺大中文系博士。曾獲林榮三文學散文獎、國藝會創
攝影|安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