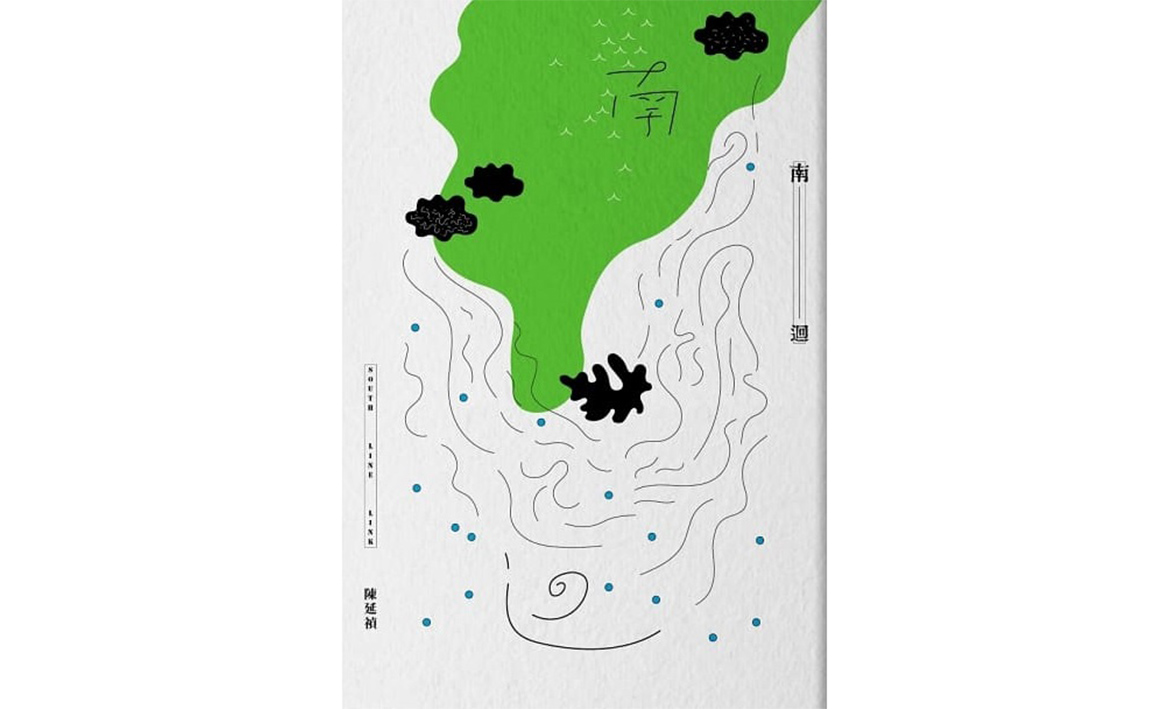主題上,《南迴》確實少見如過往的鄉土詩中那般大量對中下階層生活的特意描寫,或著墨於他者生命的悲情、苦難的遭遇,乃至是強調城鄉差距、資源分配、土地汙染等的相關的社會批判。
蟋蟀之醒,醒在一場更大的夢裡。
「像是一個島嶼/在被殖民的夢中醒來」(〈夢裡〉)
詩人所亟欲建構的「新鄉土」,其內涵所指,底是「鄉村」還是「故土」,是國族的生命史,還是個人的生命史?陳延禎在作者欄自述:「台南人,台東服役、花蓮求學,所以『南迴』。」解釋了南迴一詞乃在於註記地理上宛如節點的突進與溯源,除了指涉現實空間的移動,也涵攝著出生、服役、進修的成長歷程。陳延禎的「北」,與七、八零年代以來,南部鄉鎮青年多以台北為錨點的移動軌跡不同,「南迴」不僅是臺鐵於島嶼東南部主要幹線的名稱,自屏東枋寮到臺東,亦是詩人自臺南安定向上探及花蓮諸鄉鎮意象的鏈結。
陳延禎曾向我自述其意欲在寫實主義的基礎上,嘗試書寫 「我們這一代的鄉土」,那異於父執輩所經驗之以農漁牧業為主且相對貧苦的生活型態。我想起范銘教授如於〈後鄉土小說初探〉一文中提及後鄉土文學之特徵:「鄉土不再被認為是單一的整塊,僅相對於零星點散的城市。鄉土亦細分為區域和地方,隱含建構地方性特色、地方與地方區分特徵的態勢。」《南迴》中的「鄉土」,不惟被農田、雞舍、豬圈所包圍的臺南安定三合院,亦有著詩人旅居東部各鄉鎮的痕跡,那些受詩人主觀和情感依附之所,在詩中,先是「地方」(place)而後成為了「地景」(landscape);先是日用之物,而後成為了自我的代言;先是蟲豸鳥獸,而後成為了詩人的化身。
主題上,《南迴》確實少見如過往的鄉土詩中那般大量對中下階層生活的特意描寫,或著墨於他者生命的悲情、苦難的遭遇,乃至是強調城鄉差距、資源分配、土地汙染等的相關的社會批判,一方面,是其語言策略如楊智傑於是書序文中所說:「現實與虛構間的邏輯悖反,讓可能帶有社會批判或政治語言的元件,徹底喪失其功能、功利性,從而服務於更純粹的詩歌經驗」,另一方面,則是詩人的視角與欲與之對話的對象,除了社會弱勢如遊民、聾者之外,更多則是來到切身的人際關係與虛擬角色如偶像、動漫之上,其採取的策略是書寫自身——一農村青年的切身所見、所感以及自我身分的認同。
其所見之處,大至東華大橋、廢廟、工業風的房間、百貨公司的廁所,小至車上的博愛座、一張床、流理台、排水孔。這些事物在《南迴》中,也確實多具有一種代言的性質、心理狀態的象徵。陳延禎於《南迴》中常用的意象群,大致可以分為器物、生物兩類,器物類尤以人造的井、碗、缸、桶、罐、瓶以及床墊、流理臺為大宗,而以自然界的植物如防風林等居次,常有損、有陷、多懸危,具有承接、遮擋之意義,亦難免受人宰制與役使;生物類則以蛇、黑狗、鴿子、貓為主,而以蝸牛、燈蛾居次,常晃浪、有隔、多悲傷,具有流浪、無蹤之特徵,卻也多自由與滄桑,不斷地抵達,又離散。
《南迴》開篇第一首詩,末兩句言:
「溽熱的床有人形的沼澤/防風林的壽命將盡」
其中的幾個核心意象概念——水分(愛、傷害、勞動)、床(躲藏、休憩、歸屬、乘載)、防風林(護衛、屏蔽)——貫穿了整本詩集。床為休憩之物事、人物之載體、夢的孵化之土,上有沼澤如人物充滿飽滿的水分。
「我的床單破了洞/我藏好的眼淚/都露出來」(〈謊〉)那些水分有些來自於汗水,有些來自眼淚,床於焉成為護避之所,卻也是見證詩人危脆肉身而不得安、萎靡精神而不得眠之地。陳延禎的鄉土是和肉身連綴在一起的,床對於詩人來說,更具有生活的地方感,亦或者可看作是整座台灣之島的隱喻,孕夢之床、療傷之所,乘載著眾人的悲傷與美夢。也如同詩人說:「我要用進口的床墊/穿整套的睡衣/做最好的夢」(〈文組學生的工業風房間〉)涵納著一切的期盼、願望與夢想,床乃夢土,邊緣長著阻擋一切外來惡念的防風林。
當其言防風林的壽命將盡,所有來自海上的風都將無有遮擋的侵略過來,此前一切可供依賴、護衛的已即將失去作用了。陳延禎說:「總是害怕風/關上窗戶/沙子和掉鍊的腳踏車/並行的影子」(〈日曆〉)風帶來恐懼與傷害,是故我們也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南迴》中諸多器皿與乘載之物,會與水分有所牽連,乃因那些灌注在己身之物,無論是詩中所提及的冷飲、牛奶、舒跑、咖啡、青草茶和啤酒,或是人情互動如:「當羊毛毯乾涸如沙漠/所有的溫存都會是綠洲」(〈小病〉)、「把答案告訴我/把你水杯中的水分給我/把博愛座留給我」(〈邊緣人筆記〉)皆常與情意有關,而那份情意亦多指向充滿生機的滋潤、撫慰、關心與溫柔,那是企於對世界有所探索與溝通,卻也同時感到恐懼。
於是水分與風一樣,都會帶來傷害,尤其是那些來自「自然」的產物,如雨水、如太陽。詩人說:「你告訴我強壯有兩種/一種是被傷害/一種是被愛/那時我知道了雨真正的名字」(〈渡我〉)、「昨晚的雨像末日/淹壞阿嬤的電動車」(〈安太歲〉)、「走不到遠處的蝸牛/都被雨水壓裂」(〈冬夜散步〉)雨水成為了傷害的同義詞。又說:「我還在躲避陽光/像躲避一場雨」(〈練習事項〉)、「我撞破的毛玻璃窗/摔裂的碗/都有太陽的味道」(〈謊〉)何謂太陽的味道?詩人說:我的毛孔因烈日/崩解為蛇蛻」(〈防風林的壽命將盡〉)陽光造成膚況起塊狀的紅斑,如鐵鏽片片,帶來皮膚的繭裂、剝落以及隨之而起的刺痛感,「這些類似碗的存在/是為了到井邊/裝取與時間搏鬥/遺留的鐵鏽」(〈誰來晚餐〉)那些與破裂、崩解等皮膚相關的意象雖說來自於詩人的患病經驗,卻也在《南迴》中成為了詩人面對自我、面對世界時,所做之認識、抵抗、躲藏、和解的象徵。
正如延禎於後記中所說:
「肉體的鏽是什麼顏色?我要晒著太陽,等到顏色出現,把那些鏽的愛寫下來,把它們對我、對日子的愛通通都寫下來」
那些肉身的「鏽跡」,是先天自「母土」分離出來時在內在留下的標記,同時卻也是肉身對於後天「他者」所產生的反應,連結著先天/故土與後天/異鄉的各種生存經驗。於是乎「蛇」成為了《南迴》的主要象徵之物。此中除了蛇蛻之類比,也因「我出生/南迴鐵路剛通車,復興號是農民曆上的蛇/在延伸/到東海岸埋藏我」(〈二零一九・南迴〉),這條如蛇般蜿蜒的南迴鐵路是詩人生命歷程的紀錄與延伸。像是一種宿命,對光過敏的農村青年,生於日光烈烈的島之南境,而後又於炎炎赫赫的蓬島之東,服役、求學,在一來一返中,猶疑、追尋、抵達,而後確認自己的樣子。一切陽光對於肉身所產生的過敏反應,則是愛的浮出——關於家人的愛、故鄉的愛、世界的愛、自我的愛——愛帶來刺痛,愛如細蛇與蟋蟀,在轉瞬的快感與歡愉間,也帶來危險。
於是乎詩集中一再出現的「黑狗」,便成了詩人所選擇的化身。「整條街那麼大的黑狗/在郵局與我相望/紅著眼眶/無法傾訴他的悲傷」(〈南迴〉),看著黑狗,彷彿也看著自己。陳延禎說:「披上了整身黑就假裝已沒有太陽/假裝自己就是晚上」(〈引我〉),「黑」成為了保護色,著黑褲、著黑衣,也就能夠免於危險、勇於前行,於是「我也學他抖落雨水/用雙掌到遠方/脫下衣服/黑夜是我全新的四肢」(〈黑狗〉)。黑狗也寫詩,寫的是牠「走失的一生」(〈日曆〉),於是乎黑狗兄的新鄉土,或許也就像是在夢中觀夢,有時參與、有時抽離,詩中不再只是看到水牛與菅芒,還有戲班、金爐、雞冠花。「我離明天越來越近/離家更遠」(〈夜遊〉),在夢中,黑狗曾有歸宿,黑狗在他鄉,茫茫的大霧迎面來,充滿不確定性的明天;黑狗知道自己的來處,看盡世間的蒼涼、土地的變化,即使不安於街頭,也盡量不讓自己再受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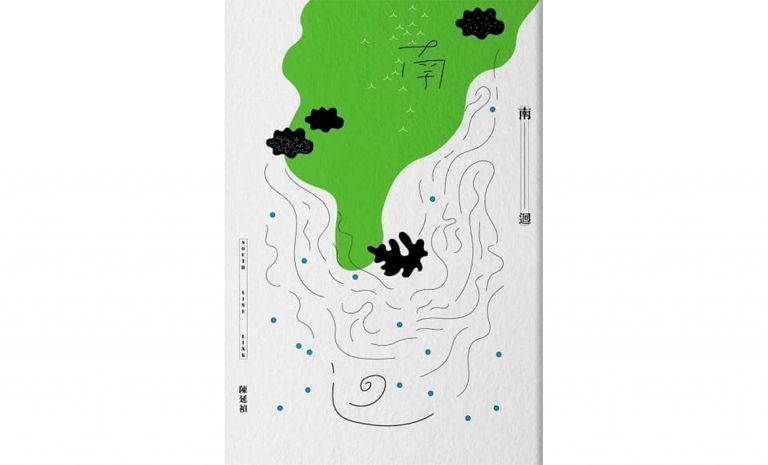
《南迴》 ,陳延禎,雙囍出版
重新回到生活的詩
《南迴》是年輕詩人由故鄉臺南往返花蓮求學沿途累積的詩作,有臺南院子裡的雞冠花,花蓮宿舍裡的工業風房間,還有翻越中央山脈此起彼落的臭青母。一面懷想原鄉的童年種種,一面憧憬離鄉背井的紛華。
無所不在的縫隙
在語言中,在生活裡,在親愛的人的臉龐,處處都充滿了縫隙。這些縫隙被一句又一句的詩行填滿,田野裡的景致,書本裡的偉大敘事,螢光幕上的少女團體,餐桌上的一道料理,統統都被寫進詩裡。當日常的巨浪淹沒我們的時刻,延禎還有餘暇刺穿碎浪的白沫,悠悠寫一行詩。
遠方的麋鹿
作為美好想像的麋鹿,三番兩次在《南迴》裡出現,牠被寄託的是未來的美好,在幽靜深邃的林間,優雅的存在。麋鹿是現代詩人心中的南山,是南迴道路上的守望者,當然,也是詩人不惜捍衛的價值觀。
文|崎雲
本名吳俊霖,一九八八年生,臺南人。畢業於臺南二中、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現就讀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班。曾獲優秀青年詩人獎、周夢蝶詩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創世紀六十周年紀念詩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及各地方文學獎等。著有詩集《回來》(角立,2009)、《無相》(斑馬線,2017)、《諸天的眼淚》(寶瓶,2020)以及散文集《說時間的謊》(臺灣東販,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