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殺夫》出版,這部被稱作「女性主義經典」的作品,在四十年後是否魅力依舊?隨著李筱涵與江炫霖的腳步,在二〇二三年重拾《殺夫》,重新去閱讀與感受,那跨越時代與性別,始終複雜的「人性」。林市所遭遇的困境或許仍在發生,在看似對女性與性更加開放的現代社會裡,女性們仍得想辦法爭取話語權——而爭搶的對象不一定是男性,也可能是如《殺夫》裡的阿罔官那樣、內化了壓抑的女性。

李筱涵
作家,台大中文系博士候選人,中研院文哲所訪問學員。曾獲林榮三文學散文獎、國藝會創作補助。作品、書評與採訪見多家報紙副刊與雜誌,著有散文集《貓蕨漫生掌紋》。

江炫霖
台大台文所碩士。Podcast帝國大學臺灣文學部成員,節目觸及文學史、當代文學、社會議題等內容。喜歡各種形式的科幻創作,關注達悟、泰雅族文學與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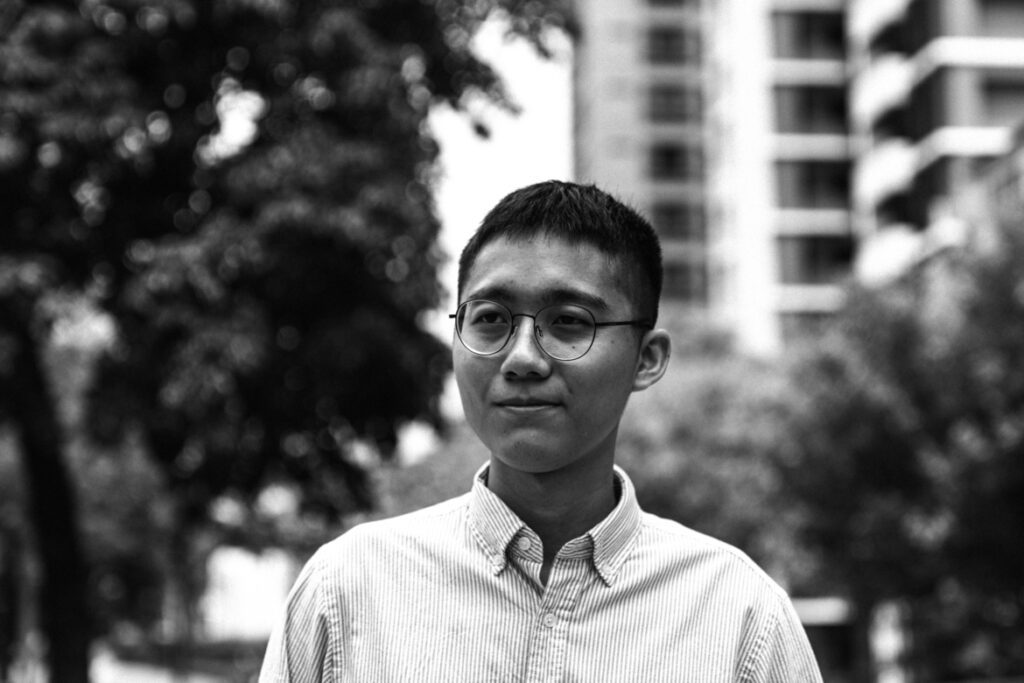
林宇軒
一九九九年生,台師大社教系與國文系畢業,台大台文所與北藝大文跨所就讀。著有詩集《泥盆紀》、《心術》,訪談集《詩藝的復興:千禧世代詩人對話》。
女性主義小說的鄉野傳奇感
林宇軒(以下簡稱軒) 今年是李昂中篇小說《殺夫》發表四十周年。我自己在研究所時第一次讀到這部作品,想問兩位是在什麼情境接觸到《殺夫》?初次閱讀時,有什麼樣的感受?
江炫霖(以下簡稱霖) 我第一次讀是因為考台文所,第二次為了錄Podcast,這次是第三次。因為是虛構的小說,而且李昂鋪排壓抑、女性主義的力道很強,主角林市和她母親在面對男性時,似乎有個世代差異,我初次讀到的感覺滿震驚的。我在閱讀時,總會覺得有種奇幻的「中國鄉土感」,彷彿這個鹿城是中國與台灣之外的異域,毫無日本統治過的感覺。
李筱涵(以下簡稱涵) 我懂這種「鄉野傳奇感」。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我們和她們的年代確實是有一段距離的?因為如果回到當時文本生成的歷史脈絡來看,其實有好幾種美學在建構。
軒 異域感可能在於,台灣應該不太會有陌生軍人突然出現在家裡。
涵 我跟炫霖差不多,也是碩班前後第一次讀《殺夫》。當時第一個印象是看「殺夫」這個標題,會設想應該是「殺」這個部分要讓我很震驚;但後來發現「夫」其實是大過「殺」的,整體父權氛圍讓女性必須「殺」才可以重生,當中的意象和畫面都非常具體地呈現恐怖的氛圍,讓我帶入女性的經驗。李昂在這裡透過主角的處境,呈現父權社會中經濟、性別、年齡多重階級弱勢的狀態。要說這是個有意識的反抗嗎?我覺得不太像是。林市最後的身心狀況都孤立無援,處於一種精神失常的狀態。不過,主角林市去「買小鴨」確實是一個有意識的反抗,她想在男性的經濟掌控之外,擁有自己生產力;最後陳江水殺掉鴨子,林市的希望也就沒有了。
霖 故事最後,進入夢境的林市和母親有所連結,但她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軒 李昂在創作《殺夫》時,是有意識地要寫一篇「女性主義」的小說。她自陳很喜歡「婦人殺夫」這個篇名,在評審的建議下才修改。我想,她將「婦人」放在「殺夫」之前,可能也有一種「女性是主動者」的構想。
涵 題目設計得很有意思,我也很想問李昂老師為什麼要改。

象徵手法之下的性壓抑
涵 林市夢中的種種象徵都和「性與死」的恐懼意象連結在一起,都是她見證、遭受暴力現場後的潛意識──無論是性暴力的「柱子」、飢餓的「口中不斷流出血」、口舌輿論的「麵線變為紫紅色的舌頭」,每個場景都導引到陳江水的殺豬場景。作為林市因受虐而精神錯亂的伏筆,李昂用夢串起來的架構非常嚴謹;而最後林市以為自己在夢中殺豬,其實是在現實殺人的反轉,讓整個悲劇的視覺衝擊非常大。
霖 我也注意到「夢境」的分量,李昂一直堆疊精神失序、餓和性的痛苦,最後被拉去殺豬……這種絕望和夢境混雜在一起的狀態,我會好奇李昂老師是不是對精神疾病有特別下工夫。另外,我也想討論這樣的作品是「現代主義」還是「寫實主義」?當中「豬」的象徵貫穿全文:女性被比做豬、女性的叫聲也被比做豬嚎叫,角色互動的過程讓我很倒胃。諷刺的是,最後陳江水被分屍,反而才是那個像是豬的對象。
涵 不討論現代主義,這很明確就是一個象徵手法。「現代主義」這個概念剛進來的時候,作家可能也並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是後面的評論者在討論時,才決定把誰拉進來。我覺得回到作家創作的年代語書寫的狀態重新思考, 會比較準確一點。李昂在夢裡面的象徵手法來指涉事實,我認為基本上還是接近寫實主義的。
霖 可能已經是內化的技巧。
軒 李昂自己對〈殺夫〉的設定在於「女性主義」,有比較多意見的是「鄉土文學」的歸類,似乎沒有太多關於「現代主義」的討論。
霖 我注意到阿罔官的角色非常立體,幾乎已經是小說的主角了,她是一個超級會操弄話語權力的說書人。你們覺得阿罔官被媳婦欺負後跑去上吊,應該要被原諒嗎?
軒 阿罔官後來把自殺當成一種談資,會強調自己「敢於上吊」,其他女性不敢。
涵 她是「真自殺」還是「假自殺」,故事沒有寫得很清楚。阿罔官的自殺是因為害怕別人怎麼說她──她沒有安全感,所以到處蒐集八卦、搶奪話語權。另一點是:守寡多年的寡婦能否有情慾?李昂寫「性壓抑」的部分是放在阿罔官身上來討論的。我覺得不能用好人、壞人、能不能被原諒來談,因為正是這個複雜面,讓阿罔官更像真實的人。
軒 阿罔官是整個故事裡最複雜的人。
霖 對,阿罔官既是受欺壓的女性,有時卻又站在講八卦、造謠的父權位置,呈現一個很立體的狀態。

是什麼原因值得重讀《殺夫》?
軒 李昂發表《殺夫》時,遭批評是「以『性』為文字遊戲的單身女郎」、「煽動報仇洩憤的殺人行為」,可以觀察到女性小說家在上世紀所面臨的處境。隨著性別意識提升,若《殺夫》發表於二〇二三年,還會引起大量討論嗎?或者說,現在才開始看《殺夫》會太晚嗎?是什麼值得現在的讀者重讀〈殺夫〉?
涵 現在比較不會有這種批評,會關注到作品中的其他面向。那個年代的社會並不會譴責加害者;對照現在#Metoo的興起,至少有一些人會覺得不應該檢討受害者。
霖 我覺得不會太晚,《殺夫》很夠格作為台灣文學女性書寫最重要的經典,我們沒辦法繞過這段歷程。「重讀」的必要性,在於「殺」這件事情是不分年代的,阿罔官表現出的權力結構在當代並沒有解決。
涵 女性會內化這個父權結構、自我審查──這個其實更嚴重,因為是無形的。
霖 剛剛比較少提到的是,這個都和民俗、宗教掛勾。
軒 但當代還會這麼重視民俗和宗教嗎?
涵 宗教在故事中是累積文化資本,教導他人的權力,象徵了人治社會之外無形的力量。
霖 現在理性、科學的思考可能取代了過往民俗的功能。
軒 《殺夫》不只是作品,也是事件,它「總結了女性的壓抑史」。
霖 金花和陳江水的情節很有趣,讓我聯想到黃崇凱《比冥王星更遠的地方》。我有想過用一個「男性文學」或「異男文學」的框架,來談男性在社會的脆弱化。
涵 現在的讀者比較會注意事件本身的議題。如果從刑法層面,精神鑑定會不會過?林市對阿罔官是不是有一種心理上的解離現象?在家暴案件、謀殺親夫、廢死議題等,都能有更多進一步的討論。這不只是「性別意識」上的提升,也是人權和生命議題教育普及後的結果,因此重新來看,這本小說所觸及的面向還是相當前衛的。
軒 我覺得如果要改編《殺夫》為電影、影集或其他形式會滿困難的,裡面太多性暴力的場景。
霖 我想到的是《返校》的恐怖感,裡面要說的女性主義的內核都還在。也許可以畫成漫畫?觀眾沒有想讀文字的話,也可以用全新的聲光效果來表現。我還有想到另一個,就是在鹿港做「文化走讀」。
涵 我覺得如果能改編成短篇劇集其實不錯,像《八尺門的辯護人》。戲劇可以從不同的視角鋪展其他角色的故事,比如阿罔官身為寡婦追尋愛情與情慾、陳江水身為豬販的勞資條件、妓女金花的生活處境、鹿城和大城市的城鄉對比等。

採訪撰文|林宇軒
攝影|朱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