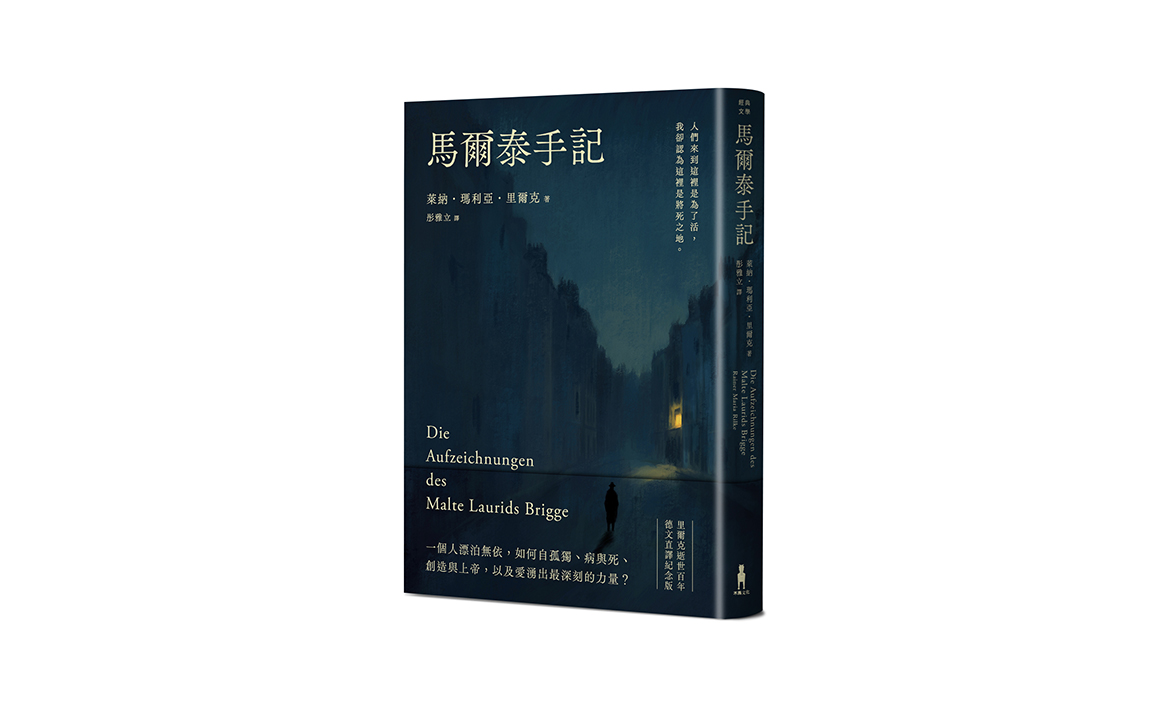一九〇二年,法國巴黎,里爾克辜負了年歲青春,逐日走向未知名的衰弱。那年他才二十八歲,正在雕塑家羅丹底下擔任秘書,學習即物,也學習看清內在。一張張顯現於巴黎街頭的臉龐,就好像日後的詩人龐德(Ezra Pound)的短詩〈在地下鐵車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人群浮光的面孔,枝枒上的濕花瓣。對里爾克來說,每看過一次面孔,即是經歷一次死亡——但死亡裡頭,似乎有什麼東西在閃閃發亮,等待他去查看。對他者的恐懼,使他完成了這本書。例如第一章節第十九頁處結尾處,主人公所說的:「我畏懼去看一張面孔的內裡,但我卻更加害怕面對一顆滿目瘡痍而沒有臉的腦袋。」整部《馬爾泰手記》提及「臉」的次數不下一百餘次。這本小說——或是用作者的話來講——長篇散文詩(long form prose poetry),與卡夫卡《審判》(Der Process)擁有同一份特質:對現實令人不安的細緻觀察。
但比起卡夫卡的懸而未決,里爾克的書寫就顯得支離破碎——沒有特定故事,彷彿漫遊,四處蒐集不幸,就如同沙特和卡繆筆下的主人公,他們不斷地追尋意義和解釋。但《馬爾泰手記》與這些現代與存在主義巨擘最大的不同是,主人公在經歷精神崩毀之時,也在慢慢地重建。「學習觀看」就是馬爾泰進行精神重建之旅的重要因素,在這個過程中,他以「超越了美醜」的方式在關照萬物,甚至從實有的物品,進展到抽象思維:死亡、愛、孤獨。
如同拉岡的鏡像(specular,但有趣的是,拉岡的鏡像論完成於這本書之後),馬爾泰在無數張臉孔中看到了他自己——被鏡像、被加倍、被死亡——他始終覺得,自己就是那個人。正如韓波(Arthur Rimbaud)所說:「我即他者」(“Je est un autre”)。在二十世紀初的巴黎,一切都在疏離,所有的面孔與鄉村別樣,都是不可靠的。也因為這種不可靠,讓馬爾泰感受到了各種壓力,他無法懸置自己的心,只能不斷藉由思辨來存活。他擔心無法言說,唯有對語言(詩性力量)的掌握,才能將他從這種恐懼和身份危機中救贖出來。
例如,死亡究竟要怎麼述說呢?馬爾泰試圖理解這一切,而這一切,必須從祖父的莊園說起:一個人打從出生起,他的身體就像一棟屋宇,死亡藍圖早已描繪在牆壁之內——他親自且仔細地,攜帶著這些藍圖,如同馬爾泰的父親,在錢包裡攜帶著克里斯提安四世的親筆死亡描述一樣,直到這座房屋被建造完成。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死亡「被物化」的過程;對於馬爾泰來說,對祖父死亡的象徵,就是房屋被拆毀,零碎地分配給生者,而馬爾泰之後會將這些建築碎片重新組裝成他自己的死亡,而他自己的死亡也將會分配給他的後代。
那麼愛呢?馬爾泰最終將愛定義為「忍受」(zu bestehen,也有存在與堅定不移之意),而被愛則意味著「逝去」,這是他成為詩人後對失落與存在的終極領悟——當我們認識了死亡,隨即就會以愛的形式,讓精神重新誕生:
Geliebt zu werden heißt, verzehrt zu werden. Zu lieben heißt, mit einem unerschöpflichen Öl zu leuchten. Geliebt zu werden heißt, zugrunde zu gehen, zu lieben heißt, zu bestehen.
被愛意味著被燒盡。愛就是——以永不枯竭的油燈製造光明。被愛的感覺轉瞬即逝,愛人的感覺則恆久持續。
——里爾克 作,彤雅立 譯《馬爾泰手記》P.320
這句寫在里爾克原稿頁面空白處的手記,接連著的,是馬爾泰對阿貝娜的情感,也是這一場漫遊的詩意終結:「被愛意味著被燃盡,去愛意味著,用一種取之不盡的油來發光。被愛意味著逝去,去愛意味著忍受。」這句作者的弦外之音,強調著「愛」是一種主動的給予,源於內在、是一種永恆的力量,不會因為付出而枯竭,並且不斷昭示著,被動接受的愛會導致自我的消融和結束。主動的愛是一種堅韌不拔的行為,能讓人確立自我並持續存在,而「被愛」的個體將被愛的熱情或強度所吞噬,最終喪失自我。
評論家斯科勒(Eleanor Skoller)認為,這本「小說」不只是散文與詩歌元素的複合體,它更像一場「理論的完成」;因為,看到不存在的事物,即是一種思辨(speculation)的形式,而當這一種思辨被「再現那缺席之物」的慾望所滋養,並且試圖將那缺席之物具體化時,我們的思辨就變成了一場理論。閱讀這本書,就是在重建馬爾泰所看見的,關於愛與死亡的理論——我們在無意之間,會對事物進行一場艱難的模擬,只因短短的一生彷彿身處暗屋,但哪怕是爐火的餘燼,都能讓我們悟出:必須對萬物與萬有充滿思辯,直到心中那事物被顯現。
撰文|曹馭博
西元一九九四年生,東華大學華文系創作組藝術碩士(M.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