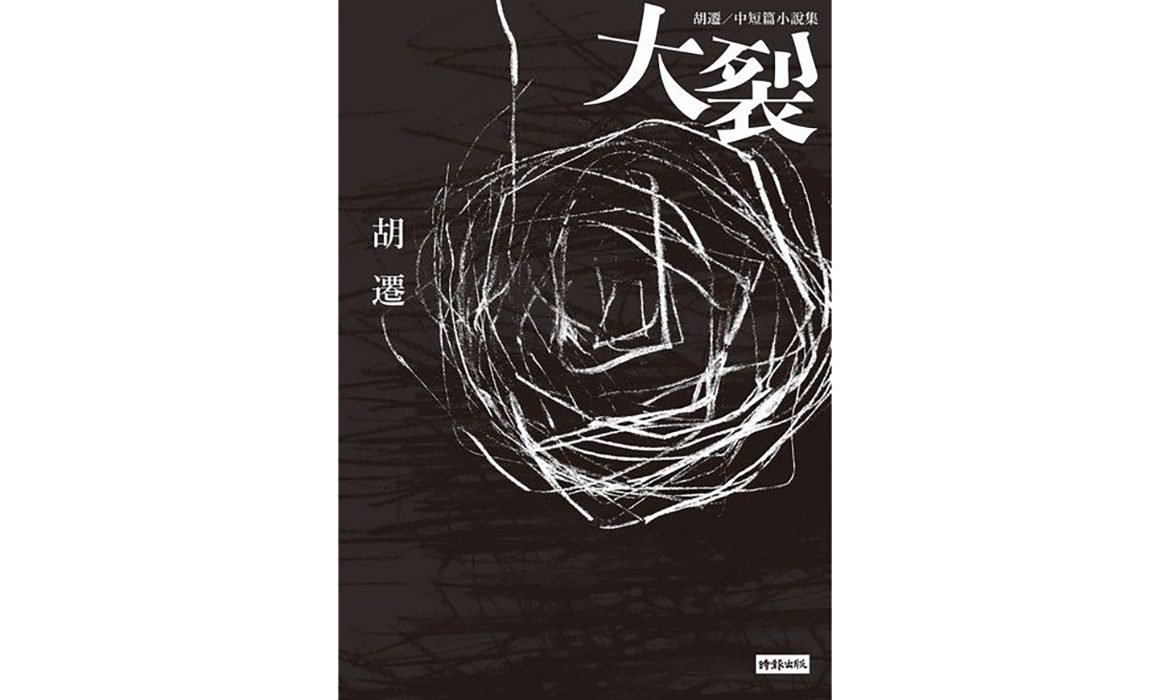中國導演胡波的電影《大象席地而坐》,在今年的金馬獎獲得了「最佳劇情片」、「最佳改編劇本」獎項之後,在藝文圈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也就在金馬獎頒布的十一月,時報出版社出版了他以「胡遷」為筆名的中短篇小說集《大裂》。一時之間,關於胡波的電影、小說和他的死亡等所有的一切,都扭攪成了「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
目前看來,大多數人都接受的一種印象是:胡波的死亡,與電影版《大象席地而坐》的製作爭議是脫不了關係的——胡波心目中的完整作品是四小時的電影,但片商擔心市場接受度,要求它剪輯為兩小時的長度。正因如此,當我帶著這樣的印象去閱讀《大裂》當中的小說版〈大象席地而坐〉時,更多了一重劇烈的反差感:這篇同名小說的篇幅極短,情節與字句的剪接都堪稱「簡斷」,處處都是毫不猶豫折斷讀者情緒預期,卻因而產生更強大張力的悍然技藝。若要打個比方,胡遷的短篇小說是一種「骨折」的文字。不,我的意思不是那種被打斷了四肢,不良於行的那種;而是以肉身硬抗鋼棍,被打得骨骼斷折,破開皮肉而出,森然而有裂齒,卻還在格鬥的那種。很痛,很硬,自知身為雞蛋也堅持要去撞高牆。如果源源本本把〈大象席地而坐〉拍成電影,依照它原來的敘事節奏,也許就是五到十分鐘的短片吧,跟四小時、兩小時這種規模都難有什麼干係;不過,小說中飄散的那種剛烈之氣,卻倒像是源源本本地在戲外應驗了。
誰讓這樣一個青年藝術家有骨折之感?或曰「社會的窒悶」,或曰「國家的暴力」,或曰「世界的傷害」。這些都可以是正解,但令人難受的是,除了這些庸俗到近乎陳腔濫調的正解,我們也很難再提出什麼更好的說法了。讀者會很清楚地看到,《大裂》當中諸篇都有著突然其來的暴力、突然其來的傷害,試著改變窒悶到不行的生活狀態。然而,光是這樣,我們並沒有辦法區別胡遷和余華,甚至也未必能區分胡遷與阿乙。余華自〈十八歲出門遠行〉起,就奠下了中國式的存在困境與暴力美學樣態。阿乙在台灣出版的《鳥看見我了》也有所繼承和突破。而胡遷則在這之上,多了一層自我解嘲:是的,我們對抗的是社會、國家、世界,但這樣的對抗又是如此陳腔濫調,數千年如一日;因此,小說中最凌厲的質問,並不是向外抗擊的內在苦悶,而是反身自割:「你以為自己就有多特別?」
當然沒有。而這就是一切自毀自傷的根源。〈一縷煙〉的畫家嫌棄室友的畫,自己畫的也只能是「延安人民歡迎您」;〈大象席地而坐〉把一切捲入的感情漩渦,最終就收束在哪裡也去不了的笨重象軀(而電影主要就是保留了這個象徵);〈氣槍〉中關於「審判」的各種辯證;〈大裂〉裡,敘事者逃避兩方陣營而去挖洞,最後還是得打成一團,並且對真正能夠「放下一切」的「叛徒」趙乃夫,有著既厭恨、又羨慕、又心知無法同路的複雜情感。〈鞋帶〉破壞了一場戲,卻也只是成就另一場戲;〈荒路〉殺了一個人,但不會有人知道、也不會改變什麼⋯⋯
例子可以舉到窮盡整本書為止,不過我們就此打住吧。如此強烈的一致性,一方面可以說是胡遷作為小說寫作者,最純粹、頑強的核心;一方面也顯示了,胡遷並不是路數很寬的寫作者。《大裂》一書的十五個篇章當中,變化的姿態不多,讀到後半會漸漸有種模式固著之感。當他那野性的鋒利文字變得可預期之後,痛還是痛的,不過讀者的感知勢必會漸漸被「馴化」的。在這樣的生命之上,加諸「路數」這種後設分析的評估,或許顯得有點冷血,但因溺愛而揚長避短,大概也不是最尊重作家的方式。畢竟在〈漫長地閉眼〉和〈張莫西去了沙漠〉等篇,我們就看到胡遷對於藝文圈的運作是如何熟稔到厭世的程度了,虛假的好評也是瞞不過他的吧。
因此,胡遷小說的長處也是他的危機所在。簡斷、鋒利、瞬間的暴力,這都是在短篇當中能夠發揮得很好的特質,但也都是一次性的特質。一旦同樣路數的篇數多了,邊際效應難免遞減。而就算是單篇內部,得獎作的大中篇〈大裂〉,就顯示胡遷在謀篇佈局的控制力遭遇了一些挑戰,反而遠比不上短篇〈大象席地而坐〉那樣精銳。胡遷擅長的是極度壓縮的短篇,而不是需要血肉的中長篇。這不是才華足不足夠的問題,而是稟賦與屬性的問題。與胡遷相比,余華都算溫吞的了;然而也正因如此,〈大裂〉在結構上的若干冗蕪與重複,也還暫時無法與《許三觀賣血記》比擬。
不過,這「暫時」當然只能成為「永久」了。這些應當是對作者說的話,現在通通只能是幹話。跟台灣頗有淵源的胡遷,不知有沒有聽過「幹話」這個詞呢?這詞有點粗俗、有點平庸、也幾乎被消費到掏空了能量,各種意義上都是一個莫可奈何的詞:我猜他也許會喜歡這個詞吧。
朱宥勳
一九八八年生,畢業於清大台文所。已出版個人小說集《誤遞》、《堊觀》,評論散文集《學校不敢教的小說》、《只要出問題,小說都能搞定》,長篇小說《暗影》,與黃崇凱共同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