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vious post
世界是什麼?我們怎麼活?《奧德賽》的希臘人說死後要出海,因為海洋就是世界盡頭;國師說你下半年要留意健康,須調整理財方式⋯⋯本期巷口新書攤,邀請從迷惘出發的詩人陳怡安與陳昌遠,為我們分享他們如何借用神話、科學、哲學、占星的語言,用詩寫下他們所理解的世界。
WH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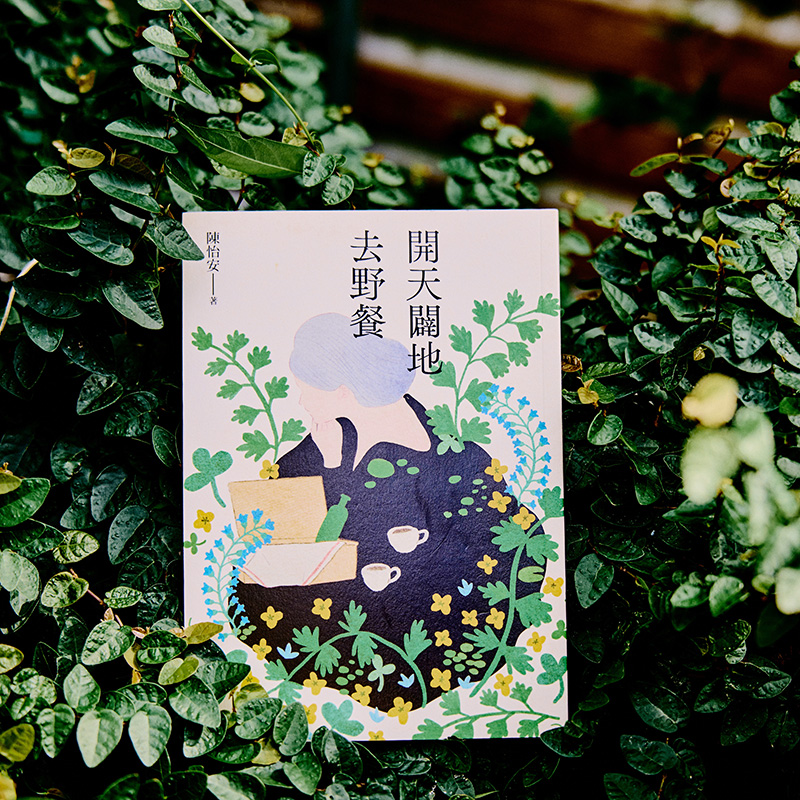
●《開天闢地去野餐》陳怡安/著・九歌出版(2025.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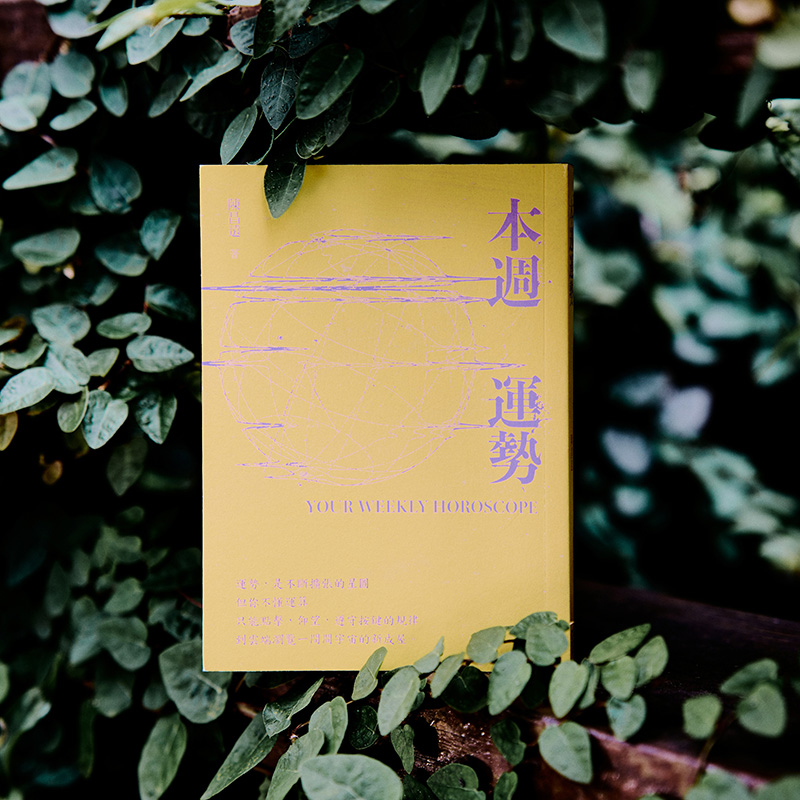
● 《本週運勢》陳昌遠/著・逗點文創結社(2025.06)
WHERE?
小小書房,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192巷4弄2之1號
WHO?
● 陳昌遠 一九八三年生,高雄小港人。高雄市立中正高工建築科畢業。曾任《中國時報》高雄印刷廠技術員,現職為《鏡週刊》人物組文字記者。曾獲楊牧詩獎、台灣文學金典獎。著有詩集《工作記事》、《本週運勢》。
● 陳怡安 週間是保育人員,週末是海邊的一天店長。畢業於中央大學中文系、東華大學華文所。曾獲葉紅女性詩獎、奇萊文學獎、紅樓詩社出版贊助,入選《2022臺灣詩選》。出版詩集《安好》、《我和我私奔》、《開天闢地去野餐》。
陳昌遠(後簡稱遠) 寫詩有時候是選擇用高度壓縮的方式,描述自己所看見的世界。我以前很常思考自己如何觀看這個世界,後來接觸到天文學,就被「觀測」這個詞深深吸引住。
很多時候,我們的觀看不一定真的涉入其中,平常滑臉書、滑Threads,看到各種議題被討論,但我並沒有想要參與,更多時候只想觀測,並透過這些刺激以新的角度思索世界。這樣的觀測,讓我對世界產生疏離感,我想把自己放到比較遠的位置,讓視角不停變動,有時候是俯角、有時候是仰望——比較常是仰望——在一定觀測的距離下,思索眼前展開的世界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發現用一、兩句話或用一本書去詮釋世界,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就只能一句一句講,講到最後,好像還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世界是什麼、也不知道自己要怎麼面對。世界充滿未知,我常在迷茫的狀態下看待很多事情,《本週運勢》就是我在迷茫中的書寫。
陳怡安(後簡稱安) 我的前一本詩集《我和我私奔》,光書名就有兩個「我」在裡面。那段時間的寫作比較自我中心,寫我的生活、我的戀愛、我的旅行,大家容易得到共鳴,但我就好像是在一個「普通女生」的追求裡。到了這本詩集,我已經受不了那個「我」,所以把它消滅掉,結果發現把自己拿掉後,看到的世界好像更寬廣了。
我很能認同昌遠說的疏離和迷惘。《開天闢地去野餐》的寫作初衷,就是想釐清「世界是什麼」,我在詩集裡大量引用不同宗教、神話,希望讓別人的世界觀進來,把自己的世界觀放得很後面、很淡薄。我更想去看、去觀察別人的世界是什麼。

安 寫作這本詩集的時候,我帶著一個很明確的問題:世界是什麼?我帶著疑問找書來看,先是找到了神話——不同族群對於創世的想像,讓我找到一個視角重新觀測世界。接著科學物理、哲學、文學,在接下來的閱讀幫助我對「世界」展開多面的思考。
閱讀首先的影響是「字詞」。我的詞彙量原本比較少,可能只知道宇宙、黑洞這些比較常見的詞,但是當我深入閱讀科學相關的書(我讀了簡易版的《時間簡史》)(遠:我也是!),諸如「夸克」的詞彙才被我看見,而寫詩讓我能透過詩意的視角看待它們。夸克、質子、中子,這些字光是唸起來就有很漂亮的聲音。一九六三年,物理學家默里・蓋爾曼爲夸克命名時先想出聲音,而沒有拼法,後來從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芬尼根的守靈夜》借用quark一詞,也就是說,科學家為這個聲音安裝上一種對世界的解釋。我後來覺得這件事很美,就著迷於把將這些很美的字當成詩的元素,納進詩歌的世界。
遠 「運勢」這件事讓我得到一個重新思考詩歌語言的起點。《本週運勢》還沒寫的時候,瑪法達(Mafalda)已經紅了一段時間,大家都在聊她寫的星座運勢,我就找來看。在讀的時候,我發現她其實動用到寫詩的語言策略,透過比喻去談愛情、金錢、工作運或人際關係,這讓我非常震驚。看見她成功使用詩的語言打動讀者,我其實有種挫敗感——我明明是寫詩的人,為什麼做不到?當然更多是不服氣,我就想說來寫看看,既然你用詩語言寫運勢,那我也要練習用占星的語言來寫詩。
當時我生活裡只要閃過什麼靈感或雜訊,就會用星座預言的方式寫下來。持續寫到兩、三年前,我發現已經寫那麼多了,就想整理成完整的作品。所以《本週運勢》的根源,其實是很遊戲性、很練習性的——借用別的語言模式來寫成詩,這也成為我給自己的詩藝鍛鍊。

遠 大家一直都說靈感要來自生活。但這件事到底要怎麼落實?我在印刷廠工作的時候,每天通勤,清晨七點跟一群人一起等紅綠燈,下班的時候遇到另一群正準備去工業區上班的機車族,當時我就在想,這些日常能不能變成靈感寫出來。因為在報紙印刷廠,凌晨工作、白天睡覺,我的世界跟現實世界完全顛倒,感覺很疏離。那時太陽花剛發生,我除了在印刷廠看當天印出的報紙,只能透過網路上激烈的紛爭認識世界。這種和世界很微妙的距離感,讓我想要把網路放進我的詩。
我在寫《本週運勢》的時候,認真思考,要用「星座語言」寫一本書,到底能寫些什麼?我就想到自己對網路、雲端、宇宙的想法,而那慢慢就變成一條線索。當我決定把它編成一本書,也覺得要把自己在那段時間的體感、挫折,還有抵抗,都放進書裡。
安 有人呼喚我的名字,好像就能讓我發現他們眼中獨特的世界。我跟聾人一起工作過幾個月,手語老師教我怎麼打手語,而我會把它們畫下來,做成手語教材。聾人不會叫我陳怡安,因為要用手語拼出人的名字很麻煩,他們會用外貌特徵幫人取名字,他們叫我「像原住民的女生」。這個叫法讓我意識到他們是透過視覺的印象,為人事物命名,而那是一個和語言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
我現在的工作有時候會跟布農族人見面,他們幫我取的布農族名字叫mulas,意思是野莓果,一種有刺的紅色莓果。他們叫我mulas的時候,我覺得很特別,因為我的中文名字是超級菜市場名,我在成長過程至少就遇過三個陳怡安(笑)。我很喜歡被其他世界觀的人取名,名字好像一道能夠進入他人世界的門,擁有名字的時候,代表那個人多少記得你,願意把你納入他生活的周遭。

Q 安 《本週運勢》整體其實滿理性的,我本來以為運勢書寫會偏向靈性學,但昌遠好像是從天文、物理出發?
A 遠 我很有意避開靈性方向的寫作。有些讀者可能是在脆弱的狀態下接觸文學,想尋求支撐自己的力量,我如果用心理相關的句子讓他們「相信我」,會讓我不太踏實,所以盡量只寫有根有據的天文知識、描述我對雲端網路的觀察。
Q 遠 「愛理性」這一輯用詩和引文拉出一條源自天文物理學、關於世界起源的線,好奇這部分的靈感來源是?
A 安 在《奧德賽》的世界裡,人死掉之後就會出海,因為他們認為海洋就是世界盡頭。我讀完之後在想,人類一步一步發現地球是圓的、察覺地球繞著太陽在轉,那個「察覺到」的人應該很暈吧?原來我們一直在旋轉。我覺得人對世界的察覺都像這樣,很自然會往一個方向發展。
採訪撰文|扈嘉仁
一九九八年清明節生,命宮天機化忌,就讀政大中文系碩士班,有詩集《食言犬》、雜文集《碎光與神像》。曾獲時報文學獎、優秀青年詩人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中興湖文學獎等獎項。第十屆楊牧詩獎得主。
攝影|林昶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