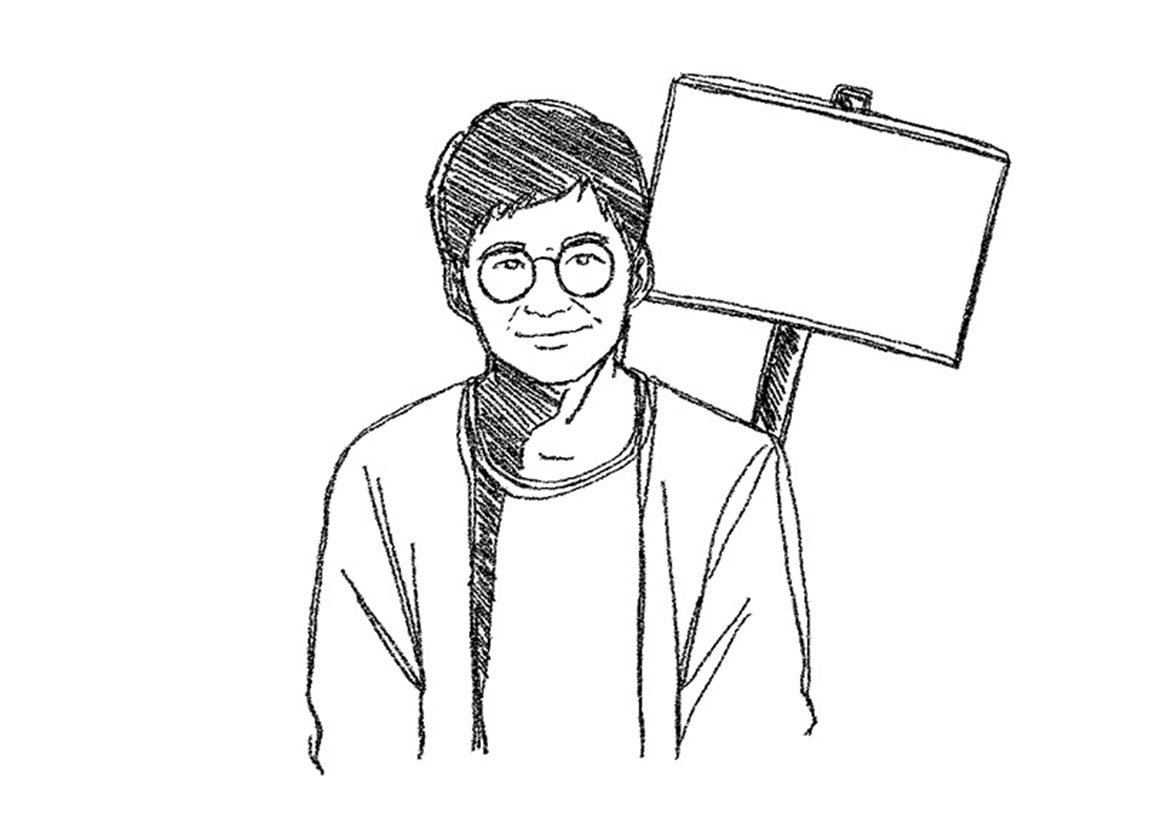大學一年級放寒假,他要回南部過年,瞹眛一段時間的校友會學姊陪他一起在野雞巴士站等車,年假前夕人潮暴滿,他和學姊排了幾小時隊,到了半夜十二點實在太累,學姊說:「我們去休息一下吧。」
成群的野雞巴士站位於大路旁的違章建築,另一側是高架橋,違章建築後方,狹窄巷弄裡密集眾多四五層樓的低矮房子,他們休息的金合歡旅社在其中一棟四樓,一樓是賣四神湯與肉包的小吃店,其它樓層掛著音響組裝,服飾修改,空壓馬達與進出口貿易公司招牌。有一座只容得下兩人並肩的電梯,一開動就左右震動,像是隨時會掉到底壓扁成廢鐵。
他沒進來過這樣的地方,非常不自在,但或許只是因為他沒跟人上過床的關係。學姊自然地說:「要休息。」穿了件紅花洋裝的大媽平淡地說:「三小時二百五。」那櫃台出奇高大,大媽像是陷在一半地穴裡,露出三分之二張臉,把房間錀匙和一個保險套從那地穴遞上來。沒有性愛經驗的他很快就射了,對過程幾乎沒有留下印象,記得最清楚的,反而是旅社的樣子,不只是櫃台,整個空間也比從外面看起來要空闊,二十幾間的房間並列在乾淨的膠皮走廊兩側,白色壁紙牆面沒有任何裝飾,完全一樣的米白色雕花木門,貼著一樣的紅色福字春聯,一樣的簡易喇叭鎖,只有塑膠刻字房號不同。房內幾乎是浪費空間似地寬大,雙人床、合併燈具控制台的梳妝桌、一整套玻璃杯放在塑膠紅盤子上、電視、冷氣機、有浴缸的浴室,甚至有一組三人座沙發、餐几,然後還剩下夠擺一桌麻將的空處。他在學姊睡去的陰暗房間裡醒來,走到窗邊,拉開輕飄飄的窗簾,底下等待野雞巴士的人潮仍然擁擠,各家顏色不同的巴士插滿大路。他覺得有什麼附在自己身上,在這個旅社裡永遠改變了自己,但或許只是廢棄了處男身份的無聊感傷而已。忽然,電話摔破東西似響起,學姊翻身接起來,「嗯,好。」她說。
寒假結束之後沒再與學姊見面,但他後來幾任女朋友年紀都比他大上幾歲,像是系上助教、老朋友或是現在公司的主管,一個有夫之婦,就像當年被什麼附身一般。如今他當然不會帶人去金合歡這樣的便宜旅館,不過他有種彆扭的怪癖,有時就是想試試自以為不會再做的事,有一次開車載了主管去金合歡旅社,他發現那群違章建築已然消失,成了一片綠地公園附停車場,他們走到金合歡旅社那棟矮樓,優雅的和風美人主管皺了皺鼻子,輕聲探問:「怎麼來這種地方?跟廢墟一樣。」他們站在一樓,小吃店拉下鐵門,那些公司招牌還在,柱子用紅漆噴上:「本棟為危險建築,即將拆除,請勿靠近」。
還好,金合歡旅社放在電梯口的燈箱仍亮著:「尚有空房,休息三小時五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