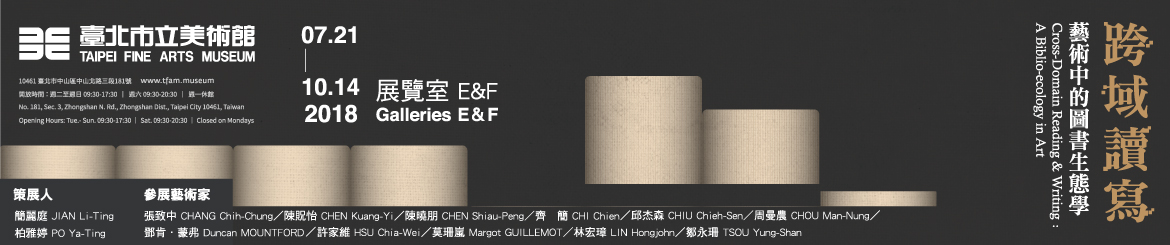6.2K
深夜酒吧裡沒有人,只有正在發呆的值班小妹和坐在吧台喝啤酒的胖姊,我也點了啤酒,笑嘻嘻說我們來看世界杯足球賽吧,今晚剛好有場轉播。我肩膀痛背也痛,整天痛,每天痛,很痛也不想回家。不想回去面對那個小小髒亂的公寓,被褥皺霉,鞋襪散了客廳,滿地的無望與孤單。
還好胖姊在這裡,還在燈下,也不肯回家。我還有同伴。
小妹扭開了老式電視,轉到足球賽,一整片綠地球場塞滿了螢光幕,還有十個高壯美男在這發光小框框內,毫不間斷地從東跑到西又從西跑到東。深夜裡屬於女子的足球賽轉播。
我發現店內角落靠窗那桌,還坐著一個長髮中年男人,在店裡見過一兩次的攝影師,聽說是酒鬼,但他不是我們這一掛的,不是熟客。他喝他的,和我們沒瓜葛。
我背好痛,唉叫了起來。胖姊搖搖頭,放下手中啤酒,幫我按摩。胖姊非常會按,好長一陣子她都幫病中臥床父親按摩身體。
胖姊的手一放上我的肩膀,我就忍不住呻吟,眼角也濕了。身體每天都痛,她的手按下之處,我覺得全身飽漲咬人的毒液,突然間有了一個開口可以流出,雖然洞很小,只滲出了一點,但終於有了希望。
以及,更裡頭有個乾澀苦楚的東西,終於感受到一點點撫慰。
嗯,啊,哼,眼淚又不自主地從眼角滑落,喉嚨發出痛苦又舒緩的嘶啞聲音。
胖姊左手繼續按,右手拿起啤酒喝了一口:「死小孩你硬梆梆的,身體裝鉛塊嗎,靠你還哭了,是我手勁太強嗎?」
「不是啦,」我邊流淚邊罵:「痛並快樂著,你快按啦!」
仁哥這時候從外頭推門進來,看我和胖姊在吧台按摩,笑著打招呼後端了酒在另一端坐下。他可能有心事,平常一定和我們玩鬧今天卻選擇遠遠坐,喔,可能看到胖姊幫我按摩,我唉唉叫,臉上還有淚痕,基於紳士風度,選擇先遠一點坐。
仁哥不看球賽的,他是寫字談國家大事的文人,體育比女生還不好,但他和我們一樣,老不想回家,和我們一樣總在這裡流連。他是自己人,是這城市暗夜在外遊蕩的鬼魂之一。
胖姊按過的地方好像有暖流通過,我全身在呼救。
我無法控制又啊啊出聲。
胖姊巴了我的頭一掌:「老娘現在繼續給你按,你以後不要每天工作到沒命,還被上司整得哭哭啼啼,每晚睡不好。你犯得著這樣活嗎你!」
那個搞攝影的突然走到吧台,站在我和胖姊旁邊。
我們嚇了一跳,但因為以前在店裡也看過他幾次,並沒太大防備。
「一起喝吧!」攝影師晃著他的酒杯。
「我們在忙,你自己喝,看看球賽吧。」我和胖姊敷衍他,沒打算和他熱絡。
「足球賽啊。」他沉默了一下,站在原地不走,抬頭望電視。
我們不理他。
胖姊又下重手,我哼了一聲從喉嚨發出濃重呼氣聲。
攝影師說:「你們在幹嘛啊……」他話還沒說完手伸過來摸我的背:「要不要跟我睡覺?」
「你走開。」我沒好氣。
他不動,還是站在旁邊。
胖姊決定無視他,繼續幫我按我那石頭般的背,這是我們的老窩,我們不看人臉色。
胖姊往我的肩胛與脊椎之間的一點按下去,我啊啊叫,五官痛得皺在一起。
攝影師突然又伸手摸我的頭髮:「要不要跟我睡覺?」
我們這次意識到這傢伙是麻煩了,卻不知道該怎麼辦,店裡就三個女生還有遠處斯文的仁哥。
搞攝影的用手滑我的臉。
「你走開啊你這傢伙,到底想幹嘛。」我甩掉他的手。
仁哥不知何時已出現在我們身邊,真兄弟,講義氣的好漢子,挺身保護朋友。
他對攝影師說:「你回位子吧,不要這樣子,這裡就讓女孩們玩他們自己的。」
攝影師推了仁哥:「你什麼東西管我要在哪裡喝!」
仁哥動氣,但沒說話,扶扶他的近視鏡框。我還在想打架真不是他這種文人的強項,就在我還沒回神的這一秒,仁哥已衝上去給了那攝影師一拳。兩人火速扭打起來,仁哥推擊攝影師的胸,沒想到攝影師是酒後鬧事老手,招數非常下賤,他側身卡住仁哥,讓仁哥無法伸手,攝影師不真的打架卻伸出另一手猛抽打仁哥的臉頰與眼鏡。
吧台內當班的小妹妹高聲尖叫,比世足賽呼聲要大幾十倍,劃破天花板。
攝影師這賤人鬆手跳開,知道繼續尖叫下去鄰居或警察要來了。
他作勢要走,冷不防又故意狠撞仁哥一下,仁哥追上去要打,他伶俐跳開。
「他媽的,什麼東西,呸。」攝影師從口袋摸出幾張皺皺的一百塊扔在吧台上,推門走出去。
仁哥搖晃地站了起來,歪掉的眼鏡就要滑落,他拿下眼鏡檢查一番,重新戴上,他衣衫扯破,頭髮散亂。
胖姊和我趕緊上前:「仁哥你還好吧,有沒有怎麼樣?」
「沒事,倒是你們都沒事?」
我感動得不得了,真是紳士,自己挨打受了驚嚇,還壓下情緒,先關心女生。
小妹重新倒了一杯生啤酒給仁哥,讓他喝冰的,定定神。仁哥這次陪我們坐上吧台,好體貼,知道要先安定我們的心。
一陣亂後,胖姊也不按了,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我也坐直,喝飲料。
驚魂未定,沒人吭聲。
逐漸地我被足球賽吸引,忘了剛剛那陣騷動。
上半場結束,進廣告。
胖姊這時才開口:「剛剛那個垃圾,揹著相機就以為是什麼攝影師,量他以後不敢來了。」
我轉身向仁哥,想說些感謝的話或安慰的話,卻驚見發現他的臉真的非常扭曲,比剛剛可怕,因為剛剛他還壓著情緒,現在是充滿真正的怒氣,比打架時候還憤怒的臉。
「你還好嗎?」我有點嚇到,這表情不像平常溫雅受女孩歡迎的他:「真的沒受傷嗎?」
他突然對我發怒:「你不知道檢點嗎?一切都是你惹出來的!」
「我?我做了什麼?我們在這邊他走過來……」
「一個女人在公開場合發出那種呻吟聲,惹得男人過來輕薄你,是你自找的,如果你端莊,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 」
我眼睛睜大,說不出話。心中的感激變成一片空白,繼而委屈,而後覺得受辱,比剛剛被那賤貨騷擾更屈辱。
但我很快冷靜下來,坐好,回頭繼續看我的世足賽。
我恢復正常了,明白了,眼前的男人也就是個世上普通男人,不是什麼紳士朋友──要是剛剛那場英雄救美,他有本事打贏了,我就不會受這種侮辱了。
◆ 本文原刊載於《聯合文學》雜誌第382期。
李維菁 小說家、藝評。著有小說集《生活是甜蜜》、《我是許涼涼》(台北書展文學大獎)、《老派約會之必要》。藝術類包括《程式不當藝世代18》、《台灣當代美術大系議題篇:商品.消費》、《名家文物鑑藏》、《我是這樣想的──蔡國強》、《家族盒子:陳順築》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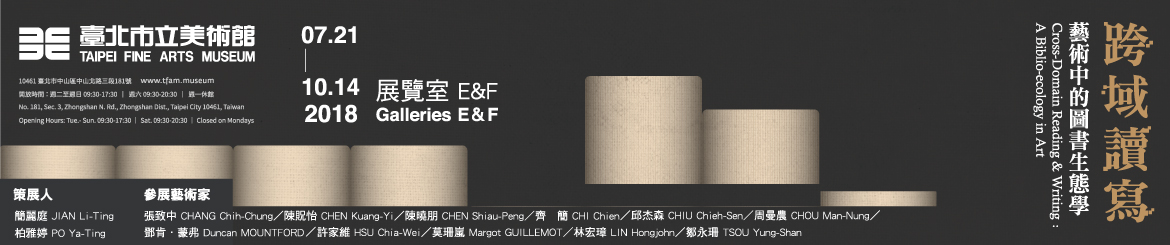
李維菁 小說家、藝評。著有小說集《生活是甜蜜》、《我是許涼涼》(台北書展文學大獎)、《老派約會之必要》。藝術類包括《程式不當藝世代18》、《台灣當代美術大系議題篇:商品.消費》、《名家文物鑑藏》、《我是這樣想的──蔡國強》、《家族盒子:陳順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