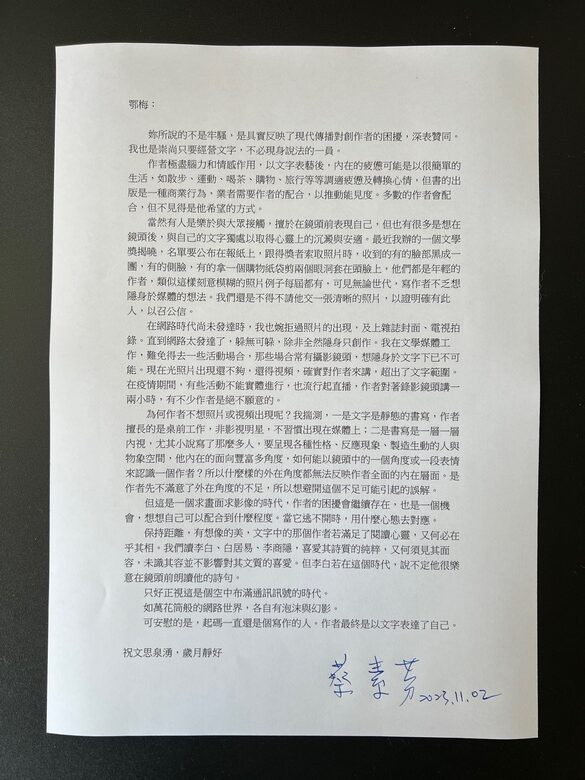歲末年終,回顧一年來的生活,每個人都有許多感觸。聯經書房.
上海書店策舉行「2023 時光手書」活動,邀請蔡素芬及姚鄂梅兩位作家寫信給對方, 聊聊屬於他們的2023年生活、創作及閱讀。信件共有四封、 兩次往返,雙方也提供生活照, 希望呈現作家在疫情下最真實的一面,與直擊內心最真摯的筆談。 希望能為 2023 年做註解,也為來年致上美好的祝福。
素芬你好!
聯經出版社的陳逸華轉給了我你的小說《藍屋子》,結果我的電腦打不開,只能在手機上看,加上是豎版,看得較慢。今天全天下雨,氣溫陡降,第一次不開空調也很舒服。接著看。簌簌雨聲中,我突然跌了進去,航海尾聲,港埠沒落,顛沛流離的物品,一步步靠近它的歸宿,那個亂紛紛的年代,幾乎難以拼湊一個完整的故事。
比起寫作,其實我更願意聊聊生活。
終於可以自由自在不戴口罩就出門了,口罩那個東西,帶給人的除了生理上的不適,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不適。好歹這一切都過去了,現在回想起來,簡直不敢相信那些事情真的發生過,我的房門被貼過封條,雖然我平時也不大外出,但真的用封條把我封在屋裡,我還是徹底崩潰了。
緊接著,樓洞口、社區大門層層封鎖,因為事發突然,生活物資短缺,貓糧貓砂斷頓,即便如此,我仍然以為是短期的,幾天,一個星期,大不了兩個星期……沒想到竟是三個月。說來荒謬,自始至終,我都沒有感染過。解封那天,我走出社區,看到足球場上的草已經齊腰深,風吹過來,巋然不動,因為那些草實在太過密實,太過強壯。
恢復並不容易,很多疫情期間關掉的店,再也沒有開起來,有時我真想通過某種管道去打聽打聽那些店主,問問他們現在在幹什麼,是不是找到新的航道了。但願對他們來說,不是恢復,而是重生,所以他們需要更多一點時間。
任何創傷都會留下後遺證。前幾天又路過那個足球場,草坪是修好了,但無人踢球,門框有些歪斜,偌大的草地上,密密麻麻全是鳥,真是好奇,既然是通過空氣和飛沫傳染,那個時候,有沒有鳥感染過心冠呢?
女人們有時候講笑話,說口罩唯一帶來的好處,是給我們省了口紅錢,因為沒有人有機會看到你的嘴,甚至是臉。
但是,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有為女人省掉口紅而叫好的聲音,哪怕是自我調侃。我覺得。
歡迎你上海,其實我們真的很近,上海飛臺北,比我飛湖北老家的時間還要短一點。
順頌秋安!
姚鄂梅
2023.9.24


小區解除封禁後第一次來到外面

封在家中琢磨簡單飲食,一菜一飯

唯一可讓我們笑出来的寶寶
女兒封在家中線上上課,煩悶至極,邊寫作業邊畫小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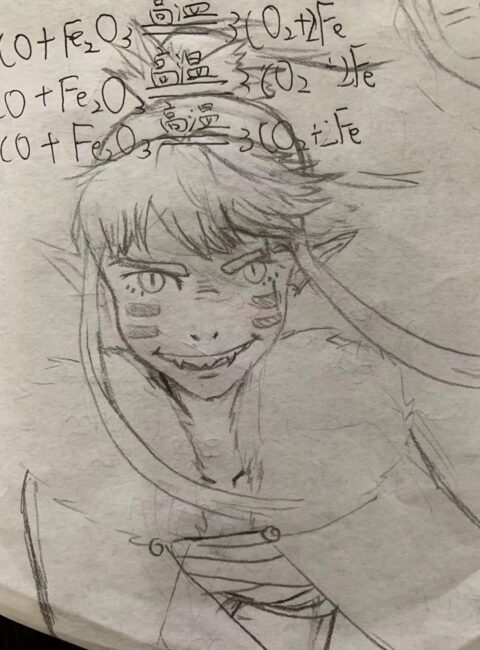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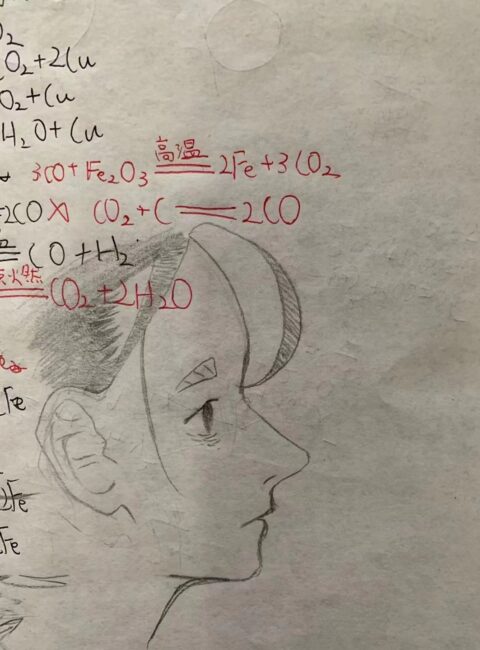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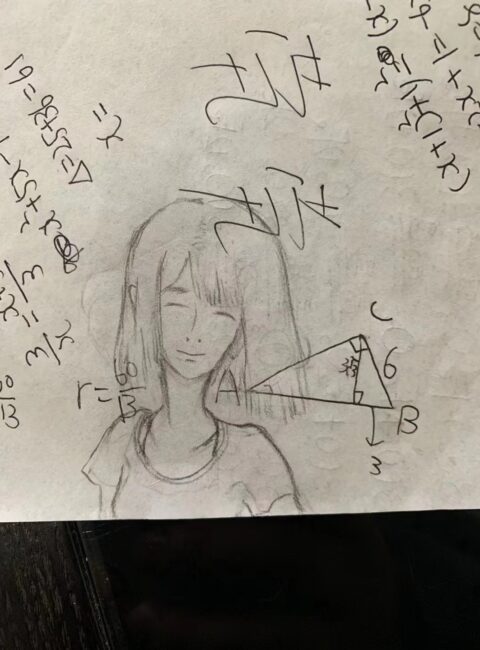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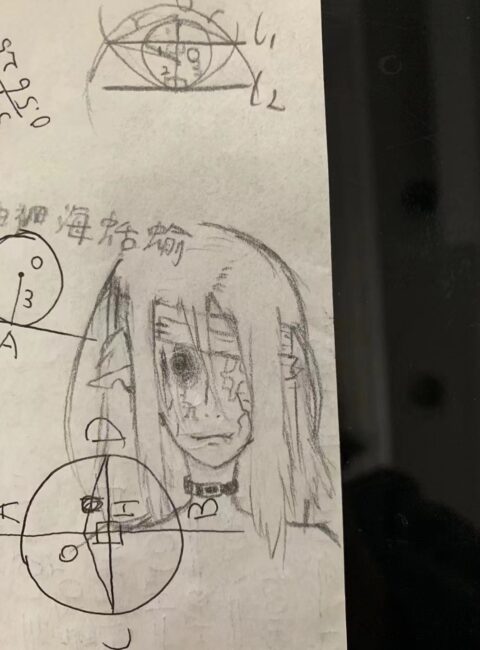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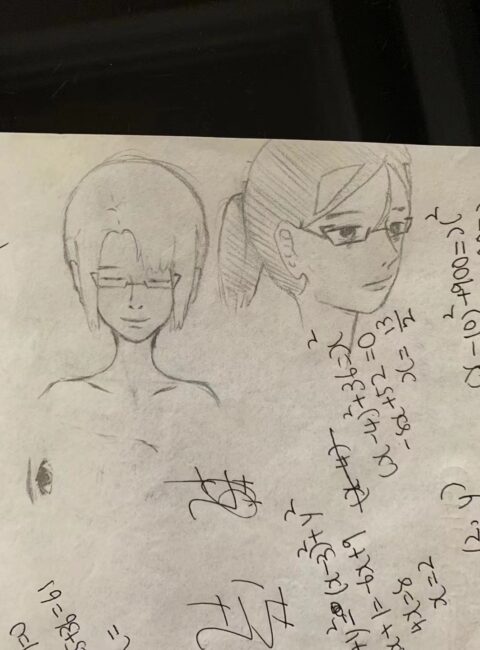
鄂梅:
收到來信時,正好我剛看完《衣物語》,腦子還留著整個故事情節的形貌,對春曦發出的撞衫撞人撞錯誤喟歎感到世事遭遇的恍惚,小說家經營人生劇場,先是把自己情感投入了,才能感染到讀者。當我把書讀完時若有所失,因為不再有後面了,故事已然結束於文字,當然不必然結束於心中,正是盪漾的餘波牽絆心間。惜在台灣暫時只能先讀到這本小說,簡體書的購買還得費些時才能送到。
我想起許多年前閱讀與張愛玲相關的資料時,曾讀到一個句子,「上海人的家當都在他的衣著上了」,那是重視衣著的表徵。時代趨遠,或已不適用,但疑問妳居住在上海,以衣物為角度切入小說,與這句話所說的衣著風尚有否關連。
信中提到的疫情生活,封條即封鎖,那情景堪可想像住所成了牢籠,絕不是我們對家的概念,心情的崩潰可想而知。平時不出門是一種選擇,而被迫不能出門是種箝制。幸得那樣的生活過去了。我的城巿在整個疫情三年期間,最緊張的大概兩個月,那期間我從事的新聞業允許在家上班,靠通訊軟體做工作上的溝通。我只在那段時間體驗到疫情的緊張感,而這緊張感並沒防礙出門,只要把口罩戴好戴滿,即使有所不便,也是防止感染的必要方式。
如今熬過三年,去年底出入關不必隔離後,我跟很多人一樣迫不及待在冬冷時節飛美,驚見美國幾個大城的機場很擁擠,九成多的人不戴口罩了,而彼時仍多確診,仗恃著疫苖的保護,人們有恃無恐的解放了自己,有些人甚至不願意打疫苖,也無礙於他們的行動,證明人們可以對抗病毒,而非被病毒打敗。那時我也把口罩取下,過一種透氣的生活。至今,我和妳一樣,不曾確診。然而零零星星的,還聽到一些友人在病毒流行的末流確診,防護有其必要,而正常生活也有其必要。
正為了正常生活的必要,人們又開始移動。機票變貴、物價變貴,生活成本變高,這段Covid-19 大流行的時代在往後的歷史,是一段不可抹滅的存在,如瘟疫之於十四世紀,流感大流行之於二十世紀初。悲傷的是,有友人死於疫情,而從染疫倖存下來的,就顯得多麼幸運可慶。疫情催促珍惜當下的領悟,想做的事應及時去做,不必期待未來會很長,於是今年四月,我又去美東,探望想念很久的十八年未見的朋友,夫婦倆住在波士頓,這趟探友之行也是感謝之旅,感謝年輕時在德州受到他們的照顧,也回望迢迢歲月在彼此留下的痕跡。
友人夫婦的帶領下,去參觀了哈佛大學、衛斯理學院、麻省理工學院,三校的校園氛圍相當不同,尤其對麻省理工學院造鎮般的學院大樓分布所凝聚的學術感染力最為震撼,思忖,若能早點體驗有這樣一個環境,讓人一走進來就想沉浸在知識探求的領域,是否人生的選擇會有所不同呢?當然所學若有不同,不代表放棄以文字表述。差別在人生投注的精力會專注在哪裡。
人生不會回頭轉個幾十年讓選擇重來,那是生理的侷限,而心理就不受時間限制。那趟旅行的省思,我回來後多讀了些理工及醫學書籍,自己把興趣延展擴張出去,也是寫作需用上的知識。學無涯,生有限。我的老朋友送我的,是還來得及追求的學習禮物。
無意中,就聊起這些了。
除了遠行,及工作上班的必要外,平日裡我也不太出門,但為了平衡坐太久的桌前靜態,我去走路,附近的校園,或幾條街道,感受安靜的風或嘈雜的巿囂。種種,亦是生活。
夜晚已略有涼意,上海緯度較高,想必涼意也漸深了。在這秋天的季節,與妳信書,多添了心頭暖色。感謝從文字認識了妳。
蔡素芬
2023.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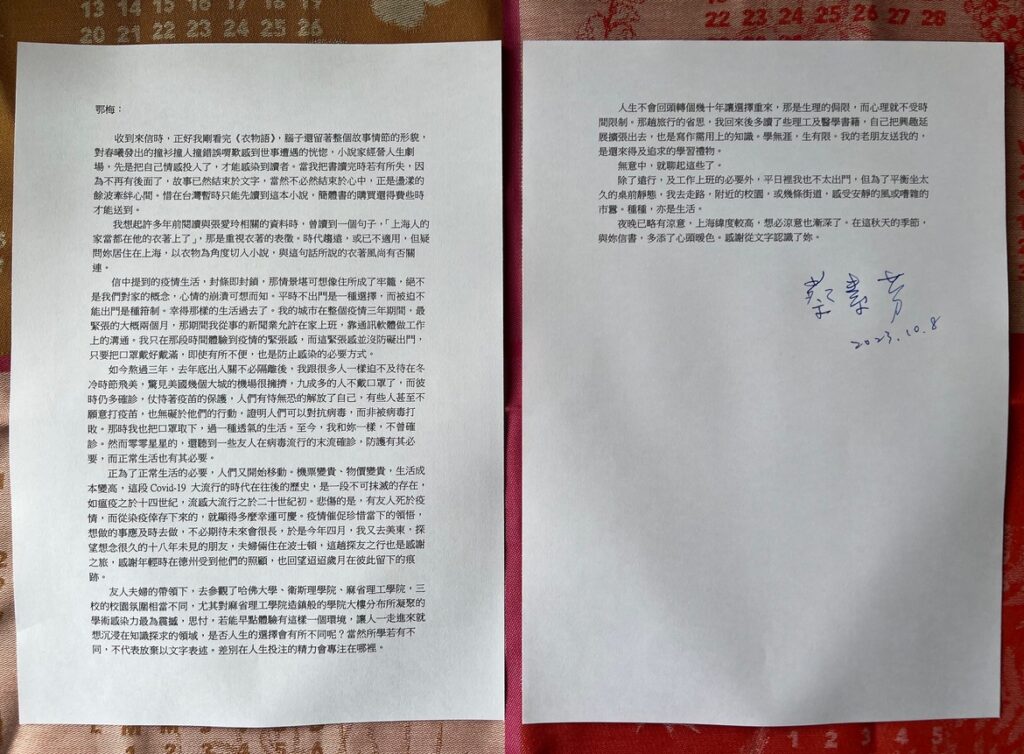
第一封書信簽名照

參訪哈佛大學,校園一景

麻省理工學院電腦大樓內景
許多幾何交集

麻省理工學院校園裝置之一
素芬你好!
我最近為一件小事煩惱。因為有書面世,出版方希望作者能拍攝一點短視頻,配合宣傳。這當然是應盡的義務,但對我來說,卻特別困難。
儘管如此,還是要硬著頭皮去做,做完了就感到非常懊惱,好像活了幾十年,突然發現自己原來如此不堪:聲音那麼難聽,長得那麼難看,表達那麼糟糕,一些自認為比較精彩的表述,通過口腔傳達出來,卻是萬分尷尬。總之,那一刻,對自己充滿深深的厭惡。
前些年,要求附上作者照片的時候,我還能勉強應付,現在要求發送視頻的機會越來越多了,各行各業都有這個趨勢。我知道很多人是喜歡也擅長拍短視頻的,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以此為生,唯其如此,我才感到不適,似乎快要不能跟上這個世界的節奏了。
有一次,我跟一個交響樂團的樂手談起這事,我覺得根源可能在於,文學,可能根本就不適合用視頻的形式來表達,無論是作者還是作品,樂手馬上反駁:不對,我也不喜歡拍攝練琴的視頻,更不喜歡有人偷拍。
也許你只是不能接受練習中的不完美。我說。
跟完美與否無關。樂手斷然否認:對我來說,練琴是絕對的私人時刻,類似於母雞下蛋,所有的母雞都是躲起來下蛋的。
我就笑了,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不錯,又何必要認識那個下蛋的母雞呢?這不是錢鐘書說過的話嗎?
看來,寫作也好,樂手練琴也好,都是端出雞蛋的行當,至於母雞,它不想露面,不想出來就那個蛋多說一二,更不會告訴任何人,它是如何醞釀那個蛋,如何生下它的,那整個過程,不可為外人語,是絕對私密、無法複製的時刻,它必須關起門窗,坦露自己,如同面對一盤裸露的泥沙,慢慢攪拌、揉捏,精心雕塑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雞蛋。直到這時,才會把門窗打開一點點,送走那個雞蛋。
這之後,作家出去運動運動,吃點東西,流一身汗,連同剛剛完成的作品一起新陳代謝出去。我就是這種人,寫完之後,很多細節都會忘記,因為我已經從心底裡把它送出去了,讓它自生自滅去了。
而樂手這邊則是千萬遍練習之後,一切記憶都明白無誤地刻進了手指,才換上華妝,隆重登場,這時,所有的拍攝者都可以打開鏡頭了。
視頻可以迅速給人留下印象,也可以迅速消失,所謂的“眼緣”真的能拉近世界的距離嗎?如果一見之下,並不能心生歡喜,豈不是無可挽回地拉開了距離?想想真是很可怕,倒不如像以前一樣保持距離,多點矜持。
不好意思,回頭一看,竟然通篇都是牢騷,實在慚愧。
秋意漸濃,珍重!
2023.10.19夜
鄂梅:
妳所說的不是牢騷,是具實反映了現代傳播對創作者的困擾,深表贊同。我也是崇尚只要經營文字,不必現身說法的一員。
作者極盡腦力和情感作用,以文字表藝後,內在的疲憊可能是以很簡單的生活,如散步、運動、喝茶、購物、旅行等等調適疲憊及轉換心情,但書的出版是一種商業行為,業者需要作者的配合,以推動能見度。多數的作者會配合,但不見得是他希望的方式。
當然有人是樂於與大眾接觸,擅於在鏡頭前表現自己,但也有很多是想在鏡頭後,與自己的文字獨處以取得心靈上的沉澱與安適。最近我辦的一個文學獎揭曉,名單要公布在報紙上,跟得獎者索取照片時,收到的有的臉部黑成一團,有的側臉,有的拿一個購物紙袋剪兩個眼洞套在頭臉上,他們都是年輕的作者,類似這樣刻意模糊的照片例子每屆都有,可見無論世代,寫作者不乏想隱身於媒體的想法。我們還是不得不請他交一張清晰的照片,以證明確有此人,以召公信。
在網路時代尚未發達時,我也婉拒過照片的出現,及上雜誌封面、電視拍錄。直到網路太發達了,躲無可躲,除非全然隱身只創作。我在文學媒體工作,難免得去一些活動場合,那些場合常有攝影鏡頭,想隱身於文字下已不可能。現在光照片出現還不夠,還得視頻,確實對作者來講,超出了文字範圍。在疫情期間,有些活動不能實體進行,也流行起直播,作者對著錄影鏡頭講一兩小時,有不少作者是絕不願意的。
為何作者不想照片或視頻出現呢?我揣測,一是文字是靜態的書寫,作者擅長的是桌前工作,非影視明星,不習慣出現在媒體上;二是書寫是一層一層內視,尤其小說寫了那麼多人,要呈現各種性格、反應現象、製造生動的人與物象空間,他內在的面向豐富多角度,如何能以鏡頭中的一個角度或一段表情來認識一個作者?所以什麼樣的外在角度都無法反映作者全面的內在層面。是作者先不滿意了外在角度的不足,所以想避開這個不足可能引起的誤解。
但這是一個求畫面求影像的時代,作者的困擾會繼續存在,也是一個機會,想想自己可以配合到什麼程度。當它逃不開時,用什麼心態去對應。
保持距離,有想像的美,文字中的那個作者若滿足了閱讀心靈,又何必在乎其相。我們讀李白、白居易、李商隱,喜愛其詩質的純粹,又何須見其面容,未識其容並不影響對其文質的喜愛。但李白若在這個時代,說不定他很樂意在鏡頭前朗讀他的詩句。
只好正視這是個空中布滿通訊訊號的時代。
如萬花筒般的網路世界,各自有泡沫與幻影。
可安慰的是,起碼一直還是個寫作的人。作者最終是以文字表達了自己。
祝文思泉湧,歲月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