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vious post
如果從林奕碩在2011年,上傳試聽帶到YouTube頻道的時候算起,百合花樂團已經出道近十五年,而生猛有勁又富含生活感的台語創作,一直是他們帶給歌迷的鮮明印象,也讓他們獲得金音創作獎和金曲獎的肯定。2024年,百合花樂團發行新專輯《萬事美妙》之後,也和Podcast頻道《BBFFMF》合作,推出一系列「台語小教室」短片,一方面宣傳專輯,同時可以推廣台語文。這是他們從音樂出發,以其他方式和台語做連結的全新嘗試。
「逐家好,我是司公鈃仔花(sai-kong-giang-á-hue)百合花的主唱……」點開百合花樂團的台語小教室第三彈「無錯篇」,主唱林奕碩、Bass手林威佐和鼓手陳奕欣以台語一一做起自我介紹,對百合花樂團來說,用台語來念團名是再自然不過了;只是,從小在家中曾和長輩說台語的林威佐和陳奕欣,其實是入團後才從林奕碩口中學得「百合花」的台語發音,而林奕碩除了是三人當中台語最好的團員之外,也是樂團創作的核心成員。
其實一開始,林奕碩曾試著以華語進行創作,但他卻一直有種「過不去」的感覺,「仔細想想,臺灣社會開始講華語,大概也就幾十年的時間,除非是京劇老師,不然掌握的華語用法其實有限。可是台語已經流傳好幾世代,無論是在菜市場或是醫院,都有機會聽到一種從沒聽過的台語用法,這是一個很『活』的語言。」林奕碩說,每當這時候,他就會拿著陌生用法到處詢問,偶爾發現台語用詞因地區不同而有差異,總讓他收穫滿滿,這樣不斷驗證、不斷學習新用法的過程,也是創作的活水與養分。
「像是某個意思我可能只會兩個字的說法,但想要塡出四個字的詞,搞不好就可以問到四個字的同義用法;或是原本想要用的字無法押韻,也可能在其他地區找到能押韻的念法。」把變化多端的台語運用在歌詞創作上,林奕碩的解釋簡白直接:「選擇很多啊!」
林威佐和陳奕欣小時候就會從家中長輩口裡聽到台語,相較之下,林奕碩則是大學學習傳統音樂後,才和台語有頻繁接觸,後來也因為想以台語創作歌詞,開始學習台語羅馬拼音與台文書寫。
「有人會問說,為什麼百合花樂團的歌詞都是台文,因為我就是這麼學的,所以如果不是用台文,我眞的不知道怎麼寫詞。」林奕碩還說,這套語言系統相當常見,就算無法理解歌詞,也不難查詢到正確字義。
而聊到語言學習,陳奕欣則說起團員間曾經的對話,他們討論過,應該要讓AI學習各種語言,尤其是像台語這類面臨流失的母語,「AI學起來很快,語言的資料庫還很豐富。」一旁的林威佐也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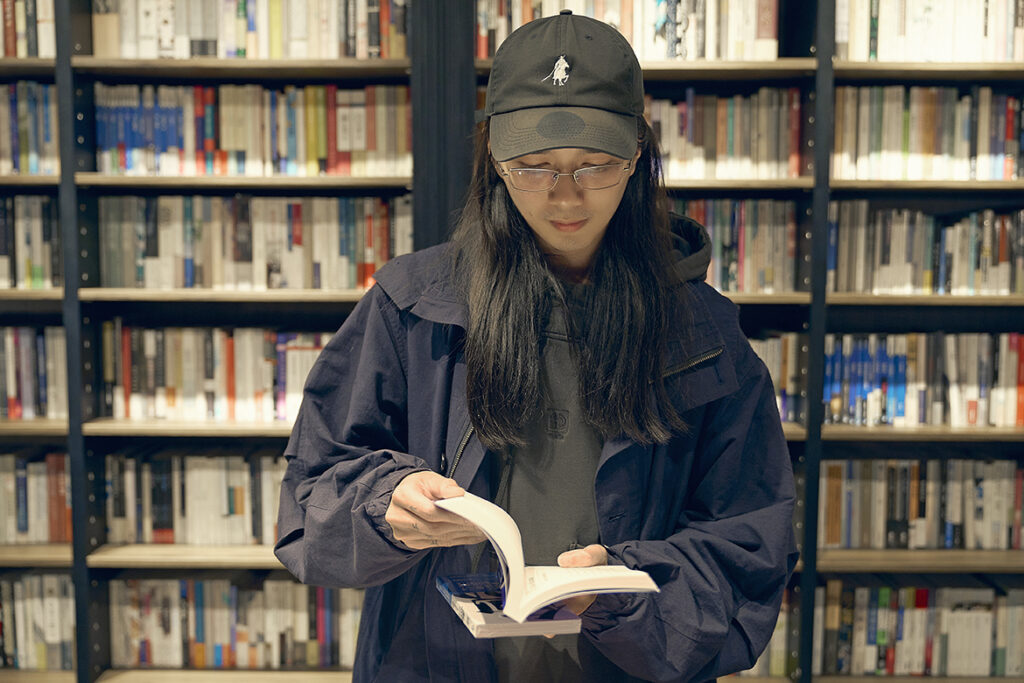

但回到林奕碩學習台語的這回事,自學的他喜歡透過早年的廣播劇、黑白電影、《豬哥亮歌廳秀》還有大量的台語歌曲,了解各個時代的台語發音與詞彙,「因為我一定要聽見聲音,光是用看的,我會很難理解。」這樣的取向,也反映了他的閱讀習慣——必須待在自己房間裡,不受到音樂和網路的打擾,才能念出聲音,吸收書中的文字。
「我也得在自己的空間裡,擁有完整的時間,把書一口氣看完。」林威佐說自己對於物理距離遙遠的故事很感興趣,最近看的書有《無懼黑暗:自願臥底納粹集中營的英雄》和《加薩日記》,這些內容的確是需要花上一點時間來閱讀。
至於三人當中隨時隨地都能看書的陳奕欣,偏好的書單大多集中在小說與人文社會類,前陣子看到朋友推薦的《渺小一生》與《臺灣漫遊錄》,一直想著要入手,而當天採訪的地點正好就在書店樓上,於是採訪結束後,她如願買下兩本心心念念的小說。林奕碩則是在架上瞧見哲學家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這本書,興奮地跟團員提及,收錄在《不是路》專輯裡的〈靈光〉歌詞,正是他將班雅明對靈光的定義翻譯而成的。
走出書店的時候,三人手上都提著剛結帳完的裝書紙袋,不禁令人好奇,百合花樂團的未來創作裡,會不會也有歌詞來自這次買的書呢?

採訪撰文|田育志
以文字為生,喜歡聽故事,也喜歡用文字把聽到的故事寫出來。不採訪的時候,會窩在家中各個角落寫稿,或是出沒在咖啡廳靠窗的座位上。文字集散地:臉書 「山田誌」。
攝影|黃禹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