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有外國訪客來到國家人權博物館,常常可以看見陳欽生前輩接待的身影。前輩謙虛地說,可能因為他是馬來西亞長大的孩子,英文剛好較流利,才有機會接觸這些外賓。他補充道,如果訪客是說日文的,通常會由蔡焜霖前輩負責。事實上,陳欽生的華語是在綠島坐監時,才漸漸學起來的;英語是他童年階段較通熟的語言。
英語帶來寬廣的世界
誰也沒能料到,這種語文條件是他捲入白色恐怖的背景因素之一,1971年陳欽生因「臺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被誣陷。當年他來臺讀大學,華語差,去美新處是為了追趕功課,其他馬來西亞僑生讀華校中學,華語根柢深,不像他讀得那麼辛苦;所以他都是一個人去埋頭苦讀。頻繁出入美新處,卻使他被鎖定為涉案者。
華語不好,其來有自。陳欽生自小被多種語文環繞,小學必須同時讀英文、馬來文和中文,中學讀英制天主教學校。家裡說客家話,在外和印尼人、馬來人玩伴說英語,和廣東人結識又學廣東話,其實他平時沒什麼機會說華語。
陳欽生說起自己幼時受的英語教育。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以前,學校考試參考英國劍橋大學的制度,所以他寫過的考題大都是英文。高中開始要讀莎士比亞,由年邁的英國籍老師授課,課堂讀的英文相當深奧,也要訓練英文寫作。「家裡面雖然沒有報紙,但老師會剪報給我們看。」陳欽生最愛的英文刊物是《讀者文摘》,地理、歷史、科技等等,主題五花八門,世界各地的時事與新知都含納其中。他甚至會寫信和外國筆友交流,彼此交換郵票。英文學養為他開啟更大的世界。
來到臺灣之後,臺南美新處的圖書館繼續餵養他對於英文閱讀的渴求,館內許多書報和雜誌從美國直送而來,當然也包含他愛不釋手的《讀者文摘》。陳欽生坦言,原本他的英語偏向英式口音,在那裡他接觸到美軍的美式英語,頗為受用。可惜這樣一個遠渡而來的僑生,勤奮學習的單純節奏,被白色恐怖打斷。進到監獄以後,還能閱讀英文嗎?如果他中文不佳,有沒有人能和他交心談話?
牢裡的英語專家
陳欽生回憶道,剛進去頭幾年,他萬念俱灰,什麼事都不想做,連跟人搭話聊天都提不起勁。在心情最差的時候,因郵包爆炸案被押的王幸男剛好來到綠島。難友們不忍見他寂寥,於是王幸男交代家人寄來厚厚一套《羅馬帝國衰亡史》英文原著和一本英漢字典,委請陳欽生幫忙翻譯。才翻不到半本,陳欽生就被調到圖書室做外役。這段時間,他轉變心境,決意好好鍛鍊自己,學點東西。圖書室裡頭上千本中文藏書,除了八股的政治書籍,他全讀遍了,同時編整出完善的借書目錄。
後來難友黃華和張星戈,還來找陳欽生學英文。同時期,在綠島有另一位英文專精者柯旗化,兩人是否有交流?陳欽生說,他們關在不同區域,未曾遇過,不過在裡頭聽說柯旗化寫的《新英文法》在書市熱銷,1983年出獄後他有去找來看,「裡面文法的結構和順序,幾乎就是我在馬來西亞讀的英文文法課本。舉的例子,我好像也有讀過。」時空交會的巧合,特別有意思。
用英文說故事
2010年左右,陳欽生開始投入人權推廣教育,不吝於講述自身經驗,也多次用英語和來自各國的訪客交流。2020年出版了英語回憶錄Facing the Calamity,並於2023年再版。為何有這系列出書的念頭?陳欽生解釋,最早是因為外國賓客來參觀,停留時間有限,往往會問有無資料可以帶回去讀。他評估自己也許有能力幫忙,便陸續完成中文的口述訪談錄,以及英文的回憶錄。
面對外國人和臺灣訪客,是否說的方式有差?陳欽生思忖道,用英語或華語來闡述,基本上不會因為語言而有內容或意涵的差異。不過,他說故事的方法確實經歷一段極為關鍵的轉型,可以說是某種心態與情緒層次的翻譯。這得從他如何說出來、走出來,種種的源頭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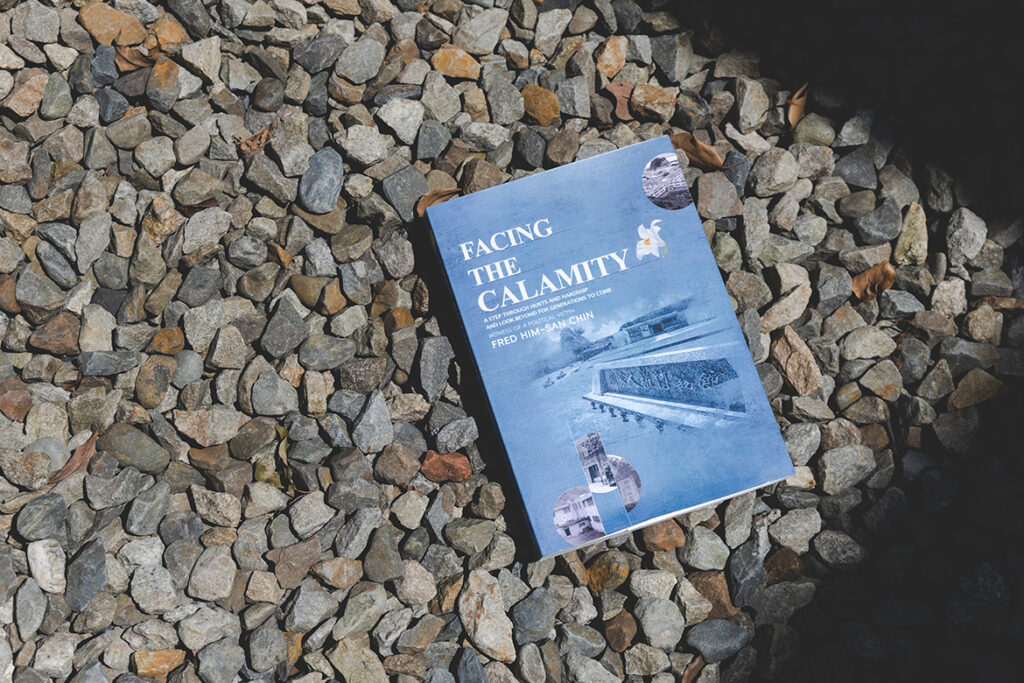
說故事帶來痛苦
出獄三年後,1986年陳欽生終於取得臺灣的身分證,1988年結婚成家令他拾回人生重心,敢於期盼未來;此後二、三十年間,受壓迫的往事被他擺在一邊,封存起來,因為唯有這樣才能若無其事地生活下去。最先找上門,說要進行訪談的是林世煜。2009年陳欽生接到林世煜來電,多次拒絕未果,最後勉為其難地答應受訪。要回溯和說出受難遭遇、被刑求關押的細節,這對陳欽生來說,痛苦萬分。
第一次訪問,僅僅觸及故事的十分之一,他就難受得講不下去;為了避開最殘忍的片段,還刻意隱瞞和修正。打開幽暗的記憶,陳欽生說,那天以後他有整整兩個禮拜,夜不成眠。只要眼睛一閉,那些景象就會重複倒帶和播放,持續困擾著他。所幸,透過一次次對人訴說,「慢慢的,睡不著覺的機會就越來越少。」哀愁似乎能夠代謝。
換一種語言說
而後和蔡焜霖前輩相識,兩人性格相近,感情要好,他們常常討論要用什麼心態面對往事。陳欽生直言,被捕、出獄到取得身分證以前,他心裡充滿了恨;遇到幾個願意幫助的人,怨懟之心才慢慢淡化下來。2010年要出面說故事時,陳欽生已在其他組織擔任志工,看到他人的慘況,知道世間苦難百態。再者,他也想考驗自己,能否承受那種回顧過去帶來的壓力。表面上,碰觸黑暗勾起的波濤,有隨時間減緩,但陳欽生一直在尋找徹底解決的辦法,舒緩講故事伴隨的後遺症。
某次,他和蔡焜霖前輩受邀到中研院分享,進而接觸到創傷理論。創傷治療師告訴陳欽生,如果他習慣帶著悲情去述說,能讓人感動,獲得同情和認可,不過自身也會受到傷害;等於要把自己反覆擺置到苦難的圖景之中。治療師接著建議他,把悲觀轉成樂觀,把負面情緒換成正面的,對聽眾先不抱期待,試看看這種說故事的方式。陳欽生個性裡有試過才知成效的執拗,他花了近兩年時間,每次要說以前,都提醒自己。好不容易,他慢慢轉變姿態。「到今天我講故事,變得沒有任何壓力。」提取晦暗回憶,不再能夠擾動他眼前的生活。陳欽生說,他只會覺得為自己愛的土地,又做了一件好事。
用歷史的觀點說
外國訪客也訝異於陳欽生的語言和心態,佩服臺灣的受難者,有辦法不帶仇恨地看待過去。陳欽生強調,控訴沒有作用,只要陳述歷史事實就好了。他直指概念的曖昧處,現今大家談論轉型正義、真相與和解。但追根究柢,每個人認定的正義可能不同;從個體出發來說,每個人遭遇過的真相為何,人們各自心底再清楚不過。所以真正應該訴求的,是社會共同的正義,是國家歷史的真相,是公眾層次的語言。「我當作這個故事是發生在某人身上的。」應和著這種核心信念,陳欽生也把他個人的苦難,轉換和翻譯成一種歷史的敘事。
西班牙怎麼面對佛朗哥政權的迫害、德國用司法制裁帶來平反、捷克和波蘭採除垢式作法,戴克拉克總統分享南非以赦免式鼓勵加害者現身,那麼臺灣的轉型正義該怎麼做?陳欽生和外賓互動時,會徵詢他國經驗,同時說明臺灣遇到的困難,以求借鏡。有些外國訪客的回答令人意外:「你們以為其他國家做得比較好,其實我們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我們的問題不會比你們的少。」而且臺灣國情不同,應有屬於自己的軌跡,很難照搬複製他國的措施。
外國訪客之中,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特別讓陳欽生印象深刻。裴洛西行程緊湊,略有疲態,但她仍然穿高跟鞋挺立,來園區了解臺灣的白色恐怖歷史。幾個月後,裴洛西特別送來感謝信,向他致意。使得陳欽生更加確信,人權推廣有其意義,尤其能讓外國人知道,臺灣的民主得來不易。
人權有跨國界的串聯,更有歷史的連綿。2010年,為了感覺自己的耐受程度,陳欽生接受曹欽榮建議,到景美看守所走走看看。事隔多年,他首次回到可怕的傷心地。他不敢進去卻又好奇地在外徘徊,這時他巧遇一位五○年代的受難者前輩,得到對方相當大的鼓舞。可惜至今陳欽生還是沒查出這位前輩的姓名,但這大概不構成遺憾,因為說故事的心意和勇氣,在他身上延續了,其中都承載著同一種歷史的語言。

法國在臺協會蒞館參訪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陳欽生(左)解說國家人權博物館成立背景

2025年3月德國班堡高等檢察署率團參訪

2024年6月加拿大智庫學者團參訪合影
文|詹斯閔
讀哲學,甘露水臺文所研究生。篇章見於《廢話電子報》等處。正在寫論文和劇本。正在祈禱創作的餘裕降臨。
圖|國家人權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