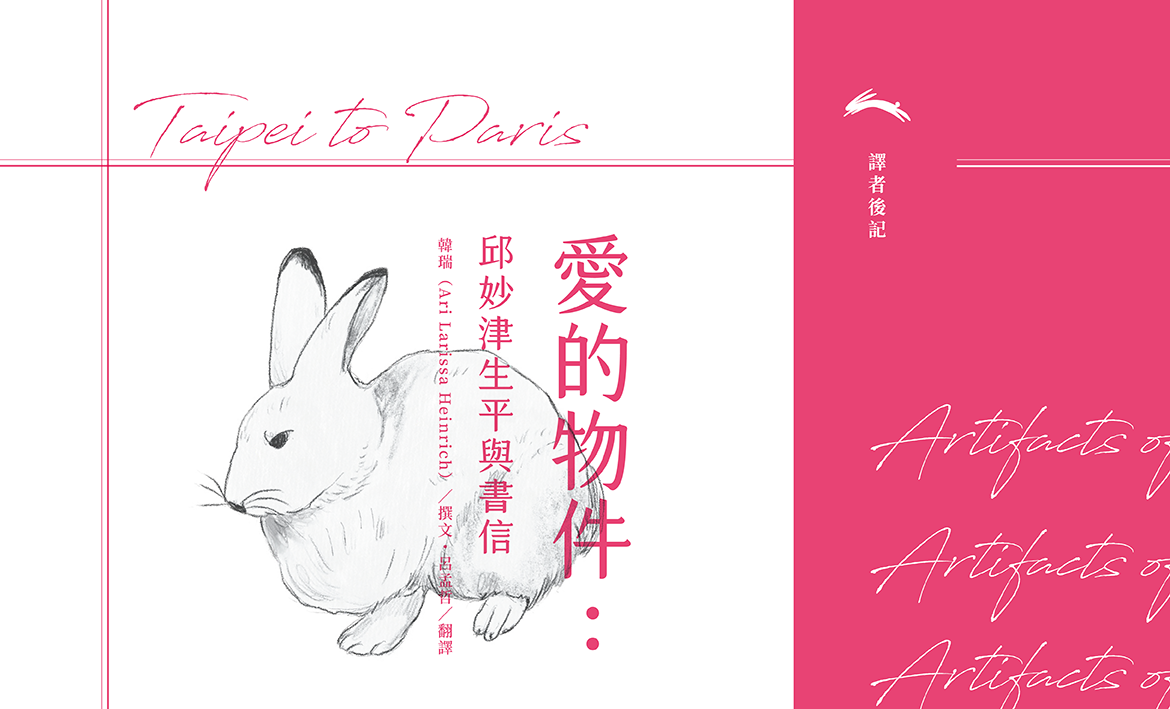《蒙馬特遺書》英譯本於二〇一四年出版時,收錄了譯者韓瑞寫下的後記,其中鉅細彌遺地介紹邱妙津的生平與創作,更爬梳台灣的歷史脈絡,讓英語讀者能更容易找到閱讀的座標。在十一年後,我們選擇摘錄後記中關於《蒙馬特遺書》的討論,一虧譯者眼中的邱妙津。
台北到巴黎
多文化、多語、文青、遠大抱負、酷兒——形容的都是邱妙津從中汲取養分、同時助以形塑的文藝圈。她短暫生命中幾個關鍵時刻也確實和此前所提、早期多個重大事件息息相關。先是十幾歲時從家鄉彰化搬到台北,進入首屈一指的女校——北一女中。一九八七年畢業時台灣剛解嚴,她進入第一學府台灣大學就讀,當時新一代作家正前仆後繼投向後現代主義懷抱,她也開始發表短篇小說,在地方報紙連載。她寫的非是純粹情愛小說,通篇多以同志情慾貫穿,書中主角常與作者本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一九八九年,二十歲的邱妙津以其中一篇小說拿到第一個文學獎《中央時報》短篇小說獎。一九九〇年,台灣第一個女同志團體「我們之間」成立,同年,她的中篇小說《寂寞的群眾》獲得聯合文學獎肯定。隔年,她取得心理學學士學位,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鬼的狂歡》。
畢業後,邱妙津曾於張老師心理輔導中心擔任輔導員,接著進入《新新聞》雜誌社擔任記者,後來到茶藝館打工,以便專心創作《鱷魚手記》。一九九二年發生臭名昭張的台視新聞事件:一名記者潛入台北某女同志酒吧偷拍並於晚間新聞播出片段,引起大眾對於「出櫃」和酷兒身分認同等議題的關注。《鱷魚手記》正是在台視新聞事件和隨之而來的爭論中完成,書中描寫一位女同志大學生和一隻「卡通人物般、無性別鱷魚」的生活,儘管「媒體大肆瘋狂猜測」,鱷魚仍決心穿著「人裝」,向公眾和媒體隱瞞牠的真實身分。全書略帶諷刺,但通俗易懂(以會說人話鱷魚為主角的小說而言已然無從挑剔了)。早在引起《中國時報》文學獎評審注意之前,《鱷魚手記》就已在酷兒圈備受推崇,書中語彙也成為某種女同志的符碼。時機無疑是邱妙津在文學界成名的重要因素之一: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她在台北找到、打造了一批對她作品接受度極高、背景多元的讀者群。
邱妙津有種罕見的天賦,在一些年輕作家身上也可以看到:那種不知從何而來、與生俱來的洞察力和野心,天才詩人韓波或可說是其中最廣為人知、讓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不過,她那早熟的洞察能力直到一九九四年離家後才得以充分發揮。二十五歲那年,她附笈前往巴黎第八大學攻讀臨床心理學和女性主義碩士,該校也正是知名女權學者西蘇(Hélène Cixous)設立的法國首個女性研究所學程——女性研究中心之所在(一九九五年邱妙津留學其間,法國政府曾威脅要取消相關計畫)。遠離台北文壇的喧囂,她全心浸淫於巴黎文化,如飢似渴地閱讀,在西蘇的著作和散文之外,也讀巴西女作家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的法語譯本、法國文學家紀德(André Gide)和小說家惹內(Jean Genet)的作品。安哲羅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和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電影則是能多看一部是一部,也對法國雕塑家蘭多斯基(Paul Landowski)著迷不已。她不斷思索如何把這些影響與自己對日本現代主義作品的喜愛相互融合,超越敘事結構常規的限制同時,還能保有藝術的真實。在巴黎,她於拼貼與創作心目中偉大作品的過程中,摒棄了《鱷魚手記》中巧妙運用的隱晦自傳式人物體,試著將小說形式的自我意識植入寫作內。最終成品難以用回憶錄或傳統書信體愛情小說歸類,創新的形式和語言也不在正統虛構作品的範疇之內。誠如《蒙馬特遺書》中所述:
我是個藝術家,我所真正要完成的是去成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我所要做的就是去體驗生命的深度,瞭解人及生活,並且在我藝術的學習與創作裡表達出這些。我一生中所完成的其他成就都不重要,如果我能有一件創作成品達到我在藝術之路上始終向內注視的那個目標,我才是真正不虛此生。
然而,隨著她不斷探索小說、文學自傳和生活實踐彼此的邊際,她的生活與創作藝術兩者的界線越形模糊,她的「敘述者」也開始每況愈下。《邱妙津日記》(2007)部分內容陷入迴圈無法自拔,更添《蒙馬特遺書》中病態的複雜程度。
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二日:我得戰勝我自己的內在,我想戰勝我自己。否則就唯有死。
死神每天都睡在我的枕頭旁。每天對我都是一個死的機會。
我得戰勝我自己的內在,走去我想去的山巔。
神啊,讓我遠離那些傷害著我的生命的東西吧,否則我會被殺死。
臨終之際,她彷彿成了一個寫作狂,不僅完成《蒙馬特遺書》手稿、一字一句細緻筆跡書寫的神祕日記,還留下了詩歌碎片、零散想法和無數封家書。遠在異鄉的親朋好友即使擔心,對於九〇年代中期在歐洲留學、生活拮据的台灣研究生來說,除了電話卡、愛心包裹,也就只有書信往返間漫長而緩慢的等待了。
邱妙津自殺的消息在台灣媒體和文壇激起許多漣漪。是為情自殺,還是為了藝術?在此特別提醒英文版讀者,自殺在東亞社會中蘊含多種文化意涵,與西方社會常見的病態、犯罪化或為神學所禁的探討模式截然不同。箇中細節在此其實無需多言,寫成一本書都不成問題,僅用戀情失敗或受到潛在精神問題所擾(蓄意自殺並特意記錄)來解釋邱妙津之死可說大錯特錯,反而該就她所希望的方式去理解她的死:視為一種言語行為,一種連結藝術與生命的終極手段。這種自殺方式不乏前例,她得以走向與偶像太宰治相同的人生道路,後者在完成實驗小說《人間失格》後不久便跳河情死;三島由紀夫事先留下手稿、安排好出版事宜後才切腹自殺。
《蒙馬特遺書》
有如歌劇般,情節誇張、預言性十足、重重設限、令人狂躁不已。一切都涵蓋在內,如若有寫遺書,我必定毫無保留,涵蓋一切在內。
但我應該不會寫。
——絲普琳格(Anna Joy Springer)《邪惡的紅色聖物,愛(The Vicious Red Relic, Love)》
讀者即便背景各異,對於由內而外講述成長故事的熟悉結構,發自內心觸探性覺醒、疏離、失落和愛等議題也能心領神會。我和邱妙津可說是同一代酷兒,《蒙馬特遺書》自然很快吸引我的注意,我們一樣,都曾於巴黎和台北讀研究所(雖從未謀面)。我很快發現,書中描繪的是一種超越身分認同、性別、種族、國家和年齡界限的內在衝突,也正是書中張力的來源。如同中國知名異議人士王〈生命與愛的極限:重讀蒙馬特遺書〉文中所述:
深陷低谷時,虛弱、心煩意亂、瀕臨崩潰邊緣,不想任何人看到,同時卻又渴望有人可以傾訴。這種時候,往往寫作變成唯一出路。雖不是面對面,卻有透過寫作才能產生的心與心的交流,藉以撐過最艱難的時刻。打從第一頁開始,我就對她有種隱晦的親密感油然而生。
自傳除了描繪出個別藝術家或作者的模樣之外,有時還能捕捉到歷史甚或小說都無法企及、獨特集體情感真實的一面或時代精神。《蒙馬特遺書》就是這樣的虛構大作:記錄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中期世界酷兒文學/文化中、尚無法以後現代主義語言所描繪的重要時刻。一個介於愛滋和網路間的奇特時光,引領我、邱妙津、其他許多作家、龐克、知識分子以及酷兒踏上一場平行旅程,既現實又形而上,從台北女同志酒吧到巴黎影院(舊金山到布拉格,倫敦到東京也都行),想方設法理解一個蠢蠢欲動、交流和存在方式已悄然轉變的全新世界。
《蒙馬特遺書》除了親暱的語調吸引人,普世的經典主題,記錄過渡時期整代人難以名狀的憂慮之外,更是一部「跨文化作品」,超脫現代華語文學常見的語言和主題侷限,無論肇因於外部或內部,或可引用文學批評大家夏志清所言,聽來或許不公,是種過於「情迷中國」的文學。儘便已歸為代表台灣的重要作家之一,邱妙津本人只認國際作家和藝術家群體(無論亡故或健在)是自己的歸屬,更進一步來說,是不受「女同志」、「華人」甚至「女人」等傳統標籤和類別束縛群體中的一員。與自己崇拜的日本和法國作家一樣,她認為自己是在和「經典」(雖以前衛派居多)的世界藝術和文學對話。
以上種種,讓《蒙馬特遺書》讀來並非易事,極盡黑暗深沉,夾雜零星歡快與幽默,以某種證言或懺悔的方式講述兩個女人關係的破裂,乃至最終敘述者的崩潰;語氣從自嘲到傲慢、從強迫性重複到崇高反思、從沉默到脆弱,不斷轉變。正文主要以人在巴黎的作者/敘述者寫給台北的愛人,以及台灣和東京親朋好友的一系列書信所組成,通篇以章節形式呈現,以心愛的寵物兔兔之死為開端,敘述者決心自殺的預告做結。我們跟隨邱妙津筆下的敘事者漫步蒙馬特街道,閱讀她與法國和台灣男女之間的風流韻事,以及文學藝術帶來的狂喜沉思。她以令人揪心卻又清晰的視角勾勒出跨越文化,或某種程度上跨性別生存的意義所在。讀者或許會注意到本書特出的文本性或物質性,對照現時數位時代的各種快速演進,書中流洩出一種獨特的「慢科技」或「類比」感。敘事充斥信件、郵票、文具、電話亭、筆記本、手寫卡片、便條、留言、遺失信封、照片,以及各式文學創作和老派溝通的文件或物證。《蒙馬特遺書》雖一再強調文本性,但獨一無二的風格恰巧正是關鍵創新所在,傳統正式文本結構幾乎全數被拋諸腦後。全書打一開始就徹底摒棄了線性敘事,其中一段引文更表示章節閱讀順序可交由讀者全權決定。各章各節不時插入名言和引文,從存在主義大師馬塞爾(Gabriel Marcel)到〈傻愛成真〉(Fools Rush In)的歌詞不等,結構顯得破碎。某些章節中,好似女性是敘述者,有些則是男性,還有一些是兩者皆非(Zöe的身分在故事中特意形塑的模棱兩可);甚或有些章節,連敘述者是誰都不清楚。小說雖然歸為某種遺書文體,但時值網路時代濫觴前夕,對我們來說也是與書信的一種告別。
大部分讀者在閱讀《蒙馬特遺書》之前,都已經知道作者於寫下該作後自殺,也正因如此,想直接解讀這部小說難度變得更高。看一本描繪自殺、作者現實生活也真的自殺的書,閱讀過程增加的繁複程度不知凡幾,但也至少表明,無論作者聲稱角色如何刻意設計或塑造,小說都摻雜一定比例的「現實主義」色彩或自傳性,與一般常說的「半自傳體」有所不同。想到《蒙馬特遺書》為邱妙津作家生涯扛鼎之作,讓人不禁興奮起來的同時,卻也難以比對、找到文本的真實指涉何在。這到底是「真實」的故事,還是虛構的敘事?敘述者是特意建構的人物,還是邱妙津的化身?一般回憶錄作者與讀者有種相互信任的關係,若以主角或敘事者的認同為切入點,本書確實讓人如墜五里霧,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此種認同苦痛相隨,卻也成就了《蒙馬特遺書》一大創新之處,即敘述者/作者毫無所懼地揭露自身最醜陋的一面,此一超越現實的「真實」在回憶錄,甚或已出版的日記中都難以得見。邱妙津不特意迎合讀者,也沒想預測政治正確的虛幻莫測。她描寫家暴和出軌場景;帶領我們陷入強迫症的無限迴圈和自我毀滅的反思;我們與她同在電話亭,看到她發狠似地用頭撞玻璃,血在臉上橫流,巴黎警方不得不介入以免造成更大的傷害。書中細緻的印象派和情色段落之一同樣映入我們眼簾——仔細看著情人的身軀在塞納河下起伏,在金黃油綠的夏日光線下躍然而起。文本醜陋之處她不願抹去,在她眼裡,同一文本也悉心記錄了尋求真理的歷程,自然同樣崇高。邱妙津小說的偉大之處,在於從沒想把讀者與醜陋隔絕;自我揭露如此赤裸裸,不看到都不行,尷尬難熬也得承擔,隨著一步步深入書中認同的世界,更會感受到隱然於後的自我憎恨、憤怒和矛盾。能如此毅然決然撕下作家真實自我的面具,或可說是三島由紀夫以來之首見。
翻譯筆記
《蒙馬特遺書》實驗性的結構和語言是翻譯過程中最大的挑戰。與預言經典的遠親《易經》相似之處在於,原著讀者往往全然按照邱妙津篇章引文指示來看待《蒙馬特遺書》:拿起書本,從任何可能的地方開始閱讀。書中找不到一個譯者可以遵循的敘事脈絡、可以預測的節奏或文風,動詞時態也不一致。同樣,按相關指示,個別句子也常陷入迴圈,脫離情節和論證常見的指向,僅剩主題還在。讀者(和譯者)除了用心體會文本呈現的各種意義之外別無他法。因而,翻譯《蒙馬特遺書》的挑戰不僅在於句法和文意的處理,試圖重現這種合作式閱讀過程更是關鍵所在。由有甚者,另一挑戰其實隱然其中,還更加重要:作為讀者,想推斷邱妙津意欲表述、更為深層的結構意義(文意本身只是暫時表達),同時想釐清文本某部分歧義的起心動念,對於其餘部分必將連帶產生一系列的果。
撰文|韓瑞(Ari Larissa Heinrich)
澳洲國立大學「澳中世界研究中心」中文媒體與文學教授,澳洲人文科學院院士。研究來自中國、台灣與香港的當代視覺文化,特別聚焦於使用生物材料(如人體部位、病理標本與有機化學物質)的實驗藝術。出版多部著作與論文,探討中國與跨國視覺文化、醫學插圖,以及酷兒理論,譯有多部二十世紀末台灣酷兒文學作品,如紀大偉《膜》、邱妙津《鬼的狂歡》與《蒙馬特遺書》。
翻譯|呂孟哲
師大翻譯所碩士畢業。現為專業中英同步/逐步口譯、中英筆譯員、中英文主持人/司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