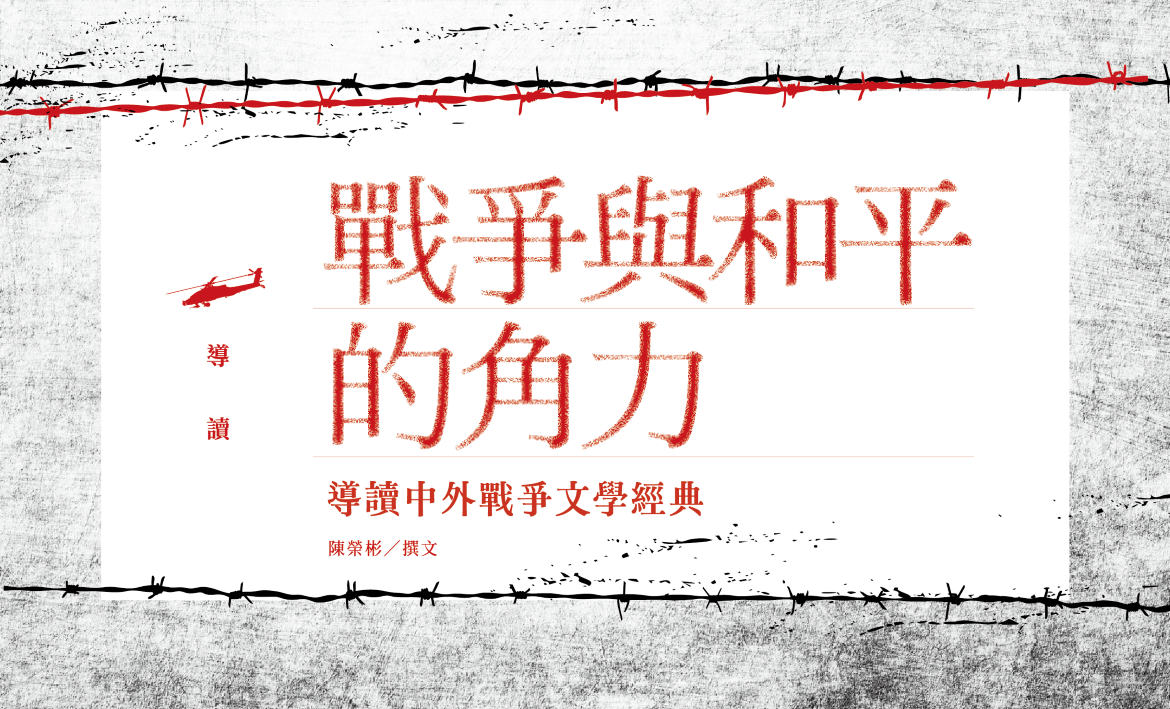「戰爭」一詞看似遙遠且陌生,但對於地處地緣政治樞紐的臺灣而言,其實戰爭從來不曾遠去。自一八七〇年代以降,臺灣每十年便被捲入一次國際衝突的風暴,這些戰事不僅改變了臺灣的政治歸屬,更衍生出至今仍未解的政治與社會糾葛,促使陳映真、黃春明等鄉土寫實主義作家,從反殖民主義的視角出發,透過小說作品對戰爭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提出深刻控訴。
十九世紀英美視角下的臺灣
十九世紀的臺灣,在東亞地區因其重要的戰略地位而頻繁地成為各國覬覦的目標。此時期的戰爭紀實,多由外國人以「第三隻眼」的視角所記錄,為後世留下珍貴的史料。雖說是史料,文本往往隱藏著深刻的個人與國家立場,因此必須從批判視角細讀才能看清這一類歷史書寫的複雜性。
《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的作者豪士是旅居日本的美國記者,一八七四年以隨軍記者身分跟著日本遠征軍來到南臺灣採訪牡丹社事件。不僅記錄了日軍攻打排灣族牡丹社、高士佛社與女奶社的軍事行動,也詳盡描寫了日方如何拉攏其他「親日」部落的手法。此外,書中還記錄下一百三十多年前恆春半島的人文風情與複雜的族群關係。雖說是新聞報導,但他的書寫並非純粹的客觀紀實,而是帶有明顯親日傾向。針對此一問題,譯者陳政三在譯註中加入了大量的考證與補充,並對豪士的觀點提出反駁。這種翻譯與校訂工作,不僅是語言的轉譯,更是一種對原始史料的「再詮釋」,旨在為讀者提供宏觀與多元的思考角度。
《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由首先將臺灣茶葉外銷國際的英國商人德陶德所作,根據他在一八八四年法國封鎖臺灣六個月期間所撰寫的日記手札彙編而成。陶德的紀錄聚焦於戰爭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特別是法軍的封鎖導致貿易中斷,使得他與其他身處北臺灣的外國人以及當地華人,都必須在無奈中「泡茶」等待戰事結束。他的敘事提供了一個非官方、非軍事的「商人視角」,從經濟與民生層面補足了官方史料的不足。書中除了記錄戰事對貿易的衝擊,也對當時的茶葉等主要外銷商品狀況有所紀錄,並對清朝將領孫開華、劉銘傳的治軍與作戰從另類視角給予不同評價。
禮密臣(又稱達飛聲)曾至北極探險,他於一八九五年以日軍隨軍記者的身分來到臺灣,親眼見證了臺灣民主國的誕生與敗亡,而後臺灣史研究者陳俊宏根據禮密臣《福爾摩沙島之過去與現在》整理成《禮密臣細說臺灣民主國》。從目錄就能看出陳俊宏試圖將這段歷史的主體從殖民者的視角改為臺灣人的抵抗與奮戰上(請注意,日本不是「接收」臺灣,而是「佔領」),才會將全書的核心內容命名為「前編:一八九五年臺灣攻防戰」,並依循時間線,詳盡鋪陳了一系列佔領事件的細節。
從國共內戰到越戰的多元敘事
臺灣文學的發展曾遭戰爭的歷史浪濤席捲,而且從現代到後現代,歷代文學家曾以不同的方式回應戰爭。這段歷史軌跡展示了一場從服務於國家意識形態的「大敘事」,逐步轉向關注個體內在掙扎與創傷的歷程,到最後甚至展現出質疑「史實」客觀性的後現代姿態。
一九五〇年代,在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下,臺灣文學史上出現了一種獨特的文學型態——「反共文學」,又稱「戰鬥文學」。這種因贊助模式而興起的文學運動以反共為主軸,並透過報章雜誌的大量刊載而盛極一時。例如,陳紀瀅的《荻村傳》便以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事件為開場,藉由主角傻常順兒的一生,描寫從晚清到共產黨佔領荻村長達五十年間的農村變遷。彭歌的《黑色的淚》則直接聚焦於國共內戰前後,青年人因政治巨浪而被捲走青春、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劇,其中〈蠟臺兒〉主角余樂德可說是那個大時代中「青年從軍」最後為國捐軀的典範。反共文學的出現是戰後臺灣特定時空背景下的產物。儘管事後看來受到審美標準過於單一化的批評,甚至被視為服務於政治宣傳的工具,但某些作家的作品還是獲得了應有的肯定,例如姜貴的《旋風》與《重陽》便是如此——後者更是精彩描寫寧漢分裂的歷史小說經典。
與反共文學的單一化審美不同,現代主義的視野以更為複雜且深刻的筆觸,批判戰爭的殘酷現實與對人性的摧殘。《臺北人》以國共內戰為背景,〈一把青〉、〈思舊賦〉與〈國葬〉等篇章都描寫各種人物在離散飄零後,蹇居臺北時充滿精神失落與文化鄉愁的內心掙扎。相較於《臺北人》並非直接描寫戰場,王文興的中篇小說〈龍天樓〉則採用類似《坎特伯里故事集》或《十日談》的敘事模式,聚焦於殘酷的戰場上,以軍中同袍為了生存而反目相向的情節揭示人性趨向背叛的低劣以及自我犧牲的高貴。
社會寫實主義作家則以在地關懷為基點,對戰爭進行直接且有力的控訴。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反映了太平洋戰爭對臺灣本土的影響,描寫在日治與戰後國府統治下,臺灣人在身分認同上的雙重困境。陳映真的短篇小說〈鄉村的教師〉則將戰爭的殘酷性推至極致,故事主角因為曾吃人肉才能在戰場上倖存,在戰後他將此祕密抖出後,因無法忍受鄉人的異樣眼光而走向毀滅。陳映真〈六月裡的玫瑰花〉與黃春明〈蘋果的滋味〉以臺灣作為美軍後援基地的背景,深刻反思美國文化與帝國主義對臺灣社會的影響,相較於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局限於國族內部的糾葛,展現出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視野。
隨著後現代小說於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興起,黃凡、張大春、林燿德、平路等文學健將在短期間展現出可觀的文學創作力。黃凡與張大春分別寫下短篇小說〈將軍之淚〉與〈將軍碑〉,前者的故事人物包括戴漢民將軍與替他參加「抗日史料研討會第五次會議」的副官馬冀,後者則是虛構出穿越時空的陸軍上將武鎮東參加自己的葬禮與「將軍碑」之揭幕儀式,無論是學術研討會或者紀念碑都具有建構史實的強烈象徵性,但誠如王德威對〈將軍碑〉提出的評論,這一類戰爭小說「將我們銘刻歷史的合理合法性轟然粉碎」。國共內戰的結束並非真正畫下句點,戰爭的餘緒深刻形塑了臺灣的社會與文化,這充分體現於齊邦媛與王德威主編的眷村文學選集《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其中,戴文采的散文〈最後的黃埔〉,描寫她的舅舅作為黃埔軍校的最後一屆畢業生,因來不及出逃,而將軍官制服與配件丟入水井,隱姓埋名,最終透過自己的努力,將人生改造為一名中醫。這類戰爭小說則是反映出「一種文化想像的解體」與「個人記憶與遺忘的糾纏散落」。
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哲學思考
在西方文學的發展歷程中,戰爭同樣是許多不朽經典的核心題材,其敘事手法從對現實的深刻哲學反思,過渡到對敘事形式本身的解構與挑戰,展現了戰爭文學的豐富性與多變性。
一九二九年,兩部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典小說同時出版,兩者雖然常被籠統地貼上「反戰文學」的標籤,但其哲學內涵遠超於此。海明威的《戰地春夢》以其最具代表性的「冰山理論」技巧創作,將戰爭的殘酷與個人的荒謬命運描寫得絲絲入扣;《西線無戰事》則是德國小說家雷馬克的代表作,則描寫戰爭如何對一代年輕人造成精神上的徹底摧毀,本書更曾受到德國納粹的強烈批判與查禁,正反映出反戰文學的力量足以讓極權政府感到威脅。
到了後現代主宰西方文壇之際,戰爭文學的敘事手法也出現典範轉移的現象。美國小說家提姆.歐布萊恩的《負重》以「後設小說」的形式角色模糊了虛構與真實的界線。他列出越戰士兵身上實際「負重」的物件清單,藉此象徵他們身上更為沉重的,無論是精神、情感或記憶的負擔。阮越清的普利茲獎作品《同情者》則將後現代主義的敘事推向另一個高峰。這部越戰小說以法越混血間諜的自白書揭開序幕,他在美國接受教育,回國後與南越部隊的許多軍官交好,但卻為北越效力。作者強烈質疑傳統的敵我二元對立,揭示了戰爭所帶來的身分認同危機以及記憶有多不可靠。此外,康拉德的《黑暗之心》雖是發表於一八九九年的現代主義小說,卻被導演法蘭西斯.柯波拉成功改編為越戰電影《現代啟示錄》,成為越戰文學經典。
歷史現場的見證與書寫
戰地記者身處歷史現場,他們不僅是資訊的傳遞者,更是戰爭的見證者。因此,他們的作品也往往擺盪於「忠於事實」與「個人觀點」之間,展現出獨特的張力。
海明威的《戰地鐘聲》脫胎於他前往西班牙報導內戰的親身經歷,以「硬漢」(code hero)人生觀創造出一個自我犧牲的虛構悲劇英雄。猶太裔烏克蘭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曾是蘇聯《紅星報》的戰地記者,他親眼見證了史達林格勒保衛戰與納粹集中營的慘狀,這也成為《生活與命運》的基礎,這本小說批判極權與戰爭對於人性的雙重壓迫,也因此曾長期遭到查禁。
戰地記者本身也具備多樣的背景與身分。大家可能只記得邱吉爾是帶領英國打贏二戰的政治家,但他不僅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寫作生涯更是由戰地記者起家,許多戰地新聞報導都收錄於《邱吉爾戰地報導:冒險犯難的年輕戰地記者》(暫譯)。俄國十月革命發生時,本身是美國共產主義勞工黨創始人的記者約翰.里德親歷歷史現場寫下《震撼世界的十天》,讓世人能更清楚俄羅斯帝國的垮台與俄共的崛起。另一位瑪莎.葛宏,不但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戰地記者之一,也是第一位女性戰地記者,更因為報導西班牙內戰而成為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戰爭的面孔》(暫譯)一書,記錄下她在歐、亞、中東、拉丁美洲等地的戰地生涯(一九三〇到八〇年代),展現出諾曼地登陸戰、納粹集中營解放等歷史現場見證者的紀實與告白。
閱讀戰爭,閱讀人性
閱讀戰爭文學是為了傳承記憶與進行反思。正如瑪莎.葛宏所言:最能嚇阻戰爭發生的不是核武,是記憶與想像。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因為資訊戰高漲、訊息氾濫,難免開始對戰爭新聞感到麻木不仁,透過導讀,我想要強調的是:戰爭文學的核心並非戰役細節,而是記錄了極端環境下的人性,文學揭示了戰爭不僅是國家間的衝突,更是人類內心深處善與惡的角力。
「戰爭文學」讓我們得以從破碎的史料中尋找連結與共鳴,從而體認和平的脆弱與珍貴,意識到人類承擔著共同的命運與責任。
撰文|陳榮彬
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已出版各類翻譯作品六十餘部,代表譯作包括梅爾維爾《白鯨記》、海明威《戰地鐘聲》與《戰地春夢》等經典文學,以及史奈德《血色大地》與歐陽泰《火藥時代》等重要史學作品。曾以年《戰地春夢》於二〇二三年獲得梁實秋文學翻譯大師獎優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