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灣出版的詩集逐漸朝著歷史敘事靠攏,例如楊智傑《小寧》、吳懷晨《渴飲光流》、廖偉棠《劫後書》,乃至於詩人向陽的新作《行旅》都擁有深探的人文歷史之關懷;關於歷史的書寫,如同墨西哥詩人帕斯所說,像一把弓與琴,弓箭射往遠方與未來,而琴聲向過去彈奏,我們得以聽到歷史的迴聲。午後的咖啡廳,詩人向陽表示前些日子才從瑞典結束詩歌朗誦會返國,便又一頭栽入各個文化單位的工作——詩人除了執筆寫作,也是關心文化之人,台灣的文化淵遠流長,其中的複雜,得靠我們所有人一起去梳理。
詩筆書寫人世三間
Q 初讀《行旅》的時候能感受到老師對於詞彙細節的講究,尤其是「詩抄」系列,對於動植物名詞的透徹與細數,有一種「詩教」的深意,如同孔子對《詩經》的見解:「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讓人不禁聯想到艾略特所說的:「詩人的第一項任務應該是使自己頭腦清晰。」老師在寫詩抄系列的時候,有什麼講究之處呢?例如風土、地誌、歷史?
A 寫地誌相關的詩作,除了詩人一開始的感動,更需要理性的觀察與人文關懷。例如看到一片海,內心除了受美景的感動之外,島嶼或鷗鳥,也是我們可以觀察的對象。詩不只是抽象的感性,更是將模糊的事物、概念、故事寫得清晰的文體。例如我曾經寫日月潭,寫在風光之下有人文色澤的邵族白鹿傳說──土地風景如果沒有人與故事,那是虛妄的;更重要的是歷史、空間、時間的交錯。我們不能只看到風景的今天,而是要知道風景的昨天。
我認為詩可以處理三種「間」:人間、時間、空間。藉由這三種不同的角度,我們可以想像,詩,始於感性,終於理智。例如我們寫玉山沿途的植物,我們就必須查找資料,並且在攀登山脈的過程中,親手摸到植物,將感官與資訊揉合在一起。我寫詩的時候偏好朝向人文景觀,例如各地的立碑或遺址,甚至是藉由一張老照片。例如我曾寫過〈嘉義街外──寫給陳澄波〉除了史料與照片之外,也要去假想陳澄波內心狀態為何;陳澄波原本是祖國派,但最後卻被當街槍殺。詩人不光只是吶喊,也要回到畫作,回到二二八發生的情境,與之對話,才能迸發出人文精神與歷史意義。
以詩的語言,開啟歷史書寫的暗箱
Q 老師的詩歌心繫土地,也在語言上帶給讀者們震撼,例如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台語詩集《土地的歌》,與當時流行的超現實主義大相逕庭,用母語帶給我們一種樸實剛毅之美。在《行旅》之中有些詩作有台語和漢語兩種版本,甚至是混搭的詩作,老師怎麼看待這兩種不同語言的書寫?或是有關於語言切換的習慣?
A 我大約在一九七六年開始寫台語詩,花了快十年的時間完成《土地的歌》,並收錄了兩首台語和「混語」的詩。例如〈在公佈欄下腳〉以公告的形式,看一行老闆的公告,勞工就罵一句訐譙(kanʟ-kiau);另一首是〈在會議桌頭前〉以王永慶的演講稿,穿插著員工在會議桌內心的訐譙。藉由權力位階較高的「國語」和「方言」互動,讓讀者知曉語言不但作為一種力量,也是權力。
這種寫法偏向後現代的語言混搭,讓兩種不同的元素造成矛盾張力;而後殖民則是透過語言混搭,抵抗強勢語言的權力,這種「混語」是同一個句子當中,所有語言的夾雜。在一九九七年左右,台灣的生活語言不斷被改變,威權年代主張標準國語,例如余光中經常主張中文書寫的原則,但大家依舊很自然地寫出自己的語言,因語言會隨著時間與社會狀態不斷演變,產出新的語彙與文法;同一個時代的語種勢必會混在一起,就像大學生說話夾雜著英文,老一輩原住民說話夾雜著日文等等,而寫詩的過程就是反應最真實的樣貌,都是在嘗試與混搭出新的感覺。我寫詩,無非是想反映九○年代至今台灣的語文狀態,有權力上的位階與鬥爭問題;到了兩千年則是相互融合──不同族群展示自己的文化。我們不能愧對母語,詩人是創造文明的巨匠,擁有母語才對詩有好處,而混語能區別出他者,也重視自己的文化底蘊。
在語言的切換之中,最困難的是語彙不足。在成語和諺語不多的情況之下,我就得回過頭學一學,並且尋找與之相符的漢字。但只要願意寫,母語的旅行就可以開始了,現在教育部有各種母語字典,各大文化單位也願意教學與分享;過去的語言政策壓抑太大,現在返回母語的過程比較辛苦,但現今的繪本、翻譯、劇場、電影慢慢擁有母語特質,是一個好的開始,混語是對母語的推新,擁有語言的多元生態,才會讓文壇更健康。


Q 我非常喜歡《行旅》之中如〈哀歌黑蝙蝠〉等關於歷史的詩作,老師於第二屆時報文學獎敘事詩獎〈霧社〉,當時黨外運動茁壯,書寫的風氣多元,除了本土歷史,漢文明的探討,也有藉由童年經驗的雜揉;該屆還有楊牧〈吳鳳〉、羅智成〈一九七九〉、楊澤〈蔗田間的旅程〉(寫糖廠的回憶與親情)、白靈〈黑洞〉(寫天安門)、陳黎〈后羿之歌〉等等。老師是怎麼看待那個時代的敘事詩呢?閱讀敘事詩、史詩、關於歷史的詩的時候,還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A 一九七九年時報文學獎增設了一個敘事詩獎,當時的副刊主編高信疆希望詩人不要再寫小詩,可以跨出腳步用長篇幅描述事件。事件未必是歷史,人生故事也是書寫的方向。我的題材涉於政治,是關於人們抗暴而亡,面對不義政權更要站起來反抗;當時正逢美麗島事件,〈霧社〉直到第二年軍事審判法庭之後才能刊登發表。當時寫霧社事件的文學書不多,大多是小說,例如張深切《遍地紅》、鍾肇政《馬黑坡風雲》、賴和的詩作〈南國哀歌〉,但我也得找專書考證,才能在史料之中想像那空白的情節與對話。我最終決定用舞台劇登場的方式呈現,用天干地支來呈現情節,並在中間後設出作者、真實人物、鬼魂的對話──在敘事方法上,我們不一定要從頭線性寫到尾,也可以將結果放置前面,一路展現各種可能。
讀者不一定能掌控歷史,但歷史的書寫包含抒情與想像的部分,能讓他們感同身受。例如歷史小說最可愛的部分在於虛構,而不是文獻的複雜,它的感動出自於虛構歷史情境,安排虛構人物與真實人物對話,用理性的創造打動讀者。好的歷史詩作,就算讀者不理解內容,可以藉由經驗而感動,例如有些讀者及其家人經歷過二二八,儘管記憶稀薄,但依舊能透過詩來感應,填補各種情緒。
詩不能離開人,儘管詩的寫法很多,例如超現實主義注重個體的內在心靈挖掘,但這份存在的意義,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呢?我想要關心他者,寫大於我的詩。寫實主義是永遠存在的,它是美學與藝術的基底。人們常常提及現代主義的書寫,其實現代主義不是單純的感性,而是詩人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去搜集資料,憑著外在景物的光影流動疊加在一起──選擇意象的背後,詩人其實知道該符號的效能,知道那些做為符號,有多重的表徵可以使用,例如我們在詩中寫一處教堂的鐘聲,它不只是現今時空的聲音,也是歷史鐘聲的反響。歷史是台灣人的本錢,不論是詩人還是小說家,都要對身邊的歷史敏感。儘管殖民是悲哀,但我們依舊要藉由書寫,去開啟不敢想像的暗箱。
Q 恭喜向陽老師受邀去瑞典舉辦詩歌朗誦會,讓台灣詩歌能夠在歐洲發光發熱。能不能與讀者分享詩歌朗誦、翻譯的經驗,以及這次的瑞典之旅?或是在這次的瑞典之旅是否有帶給你什麼靈感?或是新的體悟?
A 前些日子去瑞典時,我提供了三首台語詩,其中兩首有翻譯,另一首沒翻譯,我按照原文去朗讀,結果大家都喜歡沒有翻譯的那首詩。詩不只展現視覺修辭,也有主述者的聲響效果與表情動作,我用布袋戲聲音的口白方式展現,讓整首詩的節奏能夠吸引人。一九八五年我受邀去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聽到一位蘇聯詩人朗讀自己的詩,整整一個小時,沒有任何字幕,沒有舞蹈和音樂,甚至沒有翻譯,但每一首的聲腔都令人著迷,席間掌聲不斷。國外很注重朗誦會,不只是詩人,有時候小說家的新書發表會都會朗誦一段小說的篇章。
這次前往瑞典,原本是想去詩人馬悅然的墓前祭拜,馬悅然的妻子陳文芬女士幫我安排了在達拉納大學的演講,其後台灣駐瑞典大使館牽線,一起舉辦了朗讀會。陳文芬女士也與瑞典詩人Ingela Strandberg合作翻譯我的《四季》詩作,並將譯作寄給瑞典學院與川斯楚馬圖書館,我因而也受邀去圖書館朗誦,行程越長越多。這次帶到瑞典的詩作都寫台灣,瑞典讀者未必了解情境與歷史時空,但詩的句子通過翻譯與聲腔,一定能打動他們的心;翻譯有兩個層面,除了能被國外看到,也鼓勵年輕人繼續書寫,並讓他們有機出國增加見聞;另外就是有系統地翻譯有成就的作家,讓世界關注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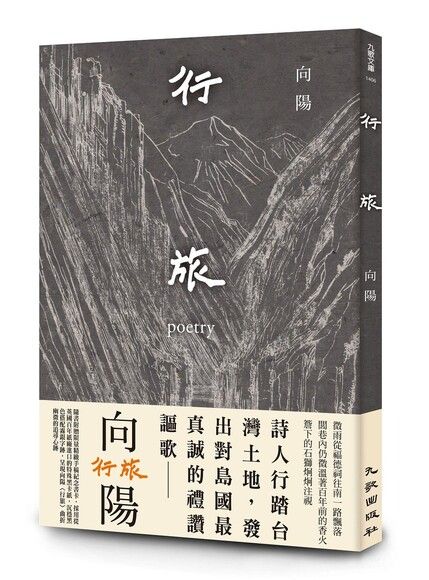
《行旅》
向陽,九歌出版
延續了《十行集》與《亂》關於本土的關懷與語言的混搭,《行旅》將書寫對象放到更細微的鳥獸草木之名與人文環境——不論是風土、地誌、歷史,詩人使自己的頭腦清晰,將萬物收攏在節奏與詩行之中,兼具寫實與現代主義的技法,將人間、時間、空間彼此疊合,不但創造出新的語言質地與複合聲腔,也呈現了台灣政治命運的坎坷與複雜性。《行旅》是一本「看見台灣」之書,能夠帶著讀者認識過去,理解現在,並且期待未來。
採訪撰文|曹馭博
一九九四年生,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新詩首獎,臺灣文學金典獎蓓蕾獎,Openbook年度好書獎。出版詩集《我害怕屋瓦》、《夜的大赦》。
攝影|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