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木下諄一的採訪約在迪化街的咖啡廳,假日午後,二樓的座位區都已客滿,排隊的顧客用不同的語言交談。翻開菜單,上頭以中英日三種語言介紹著台灣原產的咖啡和茶,在這裡談木下諄一剛出版的《日本人的台灣美味》再適合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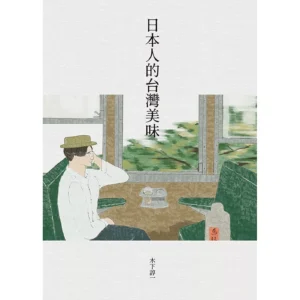
《日本人的台灣美味》
允晨文化(2025.01)
集結二十九篇在副刊連載的作品,木下諄一以長居台灣的日本人視角,藉食物為媒介,記錄他在台灣所遇見的人事物。並非將食物的美味與否奉為圭臬,這本書把食物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橋梁,寫下自身與美食氣味的記憶、情感、連結。
Q《日本人的台灣美味》是你的第四部中文作品,可否向我們談談這部作品的特殊之處以及你創作時的心境?
A 第一本小說《蒲公英之絮》是二〇一一年出版的,剛開始創作時將精力放在「摸索」,而現在則慢慢能看見作品整體的輪廓,並進一步去剪裁和修正,更注重文章的結構與節奏。《日本人的台灣美味》是將在副刊上以專欄形式連載的作品集結而成,最初專欄的名稱是「日本人與台灣美味」。即使有連載的時間壓力,我也要求自己掌握好故事的設計,每一篇在下筆前就有明確的主題,我會將主題凝縮成一句話,例如書中的〈烏龍茶〉,這篇的主題就是結尾最末的那一句「有空再來」。好的結尾能增加作品的層次,讓整篇文章有一種回甘的韻味。
Q 你曾在二〇一七年出版過日文小說《アリガト謝謝》(講談社出版),使用日文和中文創作有何不同?
A 對我來說,日文是用右手寫,中文是用左手寫。意思是,我的中文程度能說是「流暢」,使用這樣的比喻絕非難事,但與以中文作為母語的創作者相比,對於文字的掌握會較為遜色,因此我在以中文創作時會更注重情節的安排與作品的結構,這些文學技術是超越語言的。
我出版的作品以中文為主,這是因為我在台灣生活超過四十年,我相信一個寫作者必須從實際的生活經歷出發,才能書寫一個地方的事物。我在這塊土地上的時間比許多年輕人都長,我想將所看到的記錄下來。《アリガト謝謝》之所以改以母語寫作,是希望從日本人的角度探究台灣在日本發生三一一大地震時,對日本的捐獻與幫助,考量到題材才決定以日語寫作。文學還是要回到語言本身。


Q 在《日本人的台灣美味》的序中提到,這本書並非以「美食家」自居,食物美味與否並非敘事重點,而是把食物作為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書寫彼此之間的記憶、情感、連結。為什麼選擇食物作為這個系列的切入點?這個構想又是怎麼開始的?
A 這個靈感來自我開設的YouTube頻道「超級爺爺 SuperG」,頻道主要的兩個系列是「口袋名單」和「台灣美食」,是從早期美食外景節目風格的拍攝風格延伸,並做出變化。和副刊談連載的企劃時,想以「食物」為切入點去書寫一個日本人對台灣的觀察。由於剛來台灣時曾在《臺灣觀光月刊》擔任總編輯八年,我非常明白食物如何作為一種觀看的方式。
回到自身的創作,同樣是以食物作為題材,但在影片以及文字兩種不同媒介的創作中,我都採用了與觀光雜誌完全不同的視角去切入——食物只是媒介,背後所蘊含的「人的情感」才是重點。《臺灣觀光月刊》的工作經歷除了題材外,也影響了我創作過程及方式,例如影片要做企劃腳本、攝影、編輯剪輯、數據分析,這都是從前在編雜誌時習慣的工作模式,而在副刊連載時,也會考量媒材的差異,依照受眾不同去調整風格;即使同樣以食物作為切入點,影片和文字由於受眾不同,創作的風格也會不同。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日本人的台灣美味》中結尾的斟酌、調整篇幅的架構這些細節,都是我在連載過程中不斷嘗試與逐步修正的結果。
Q 在「超級爺爺 SuperG」的影片中,能感受到老師吃到美食的喜悅;〈永和豆漿〉中也描述乘客因為吃完永和豆漿而恢復了精神。在不同的媒介中,你都提到人們從食物中得到力量的故事。你個人是否曾有感受到「食物的力量」的時刻?
A YouTube頻道的「口袋名單」系列有個特色,是我會先採訪對方的經歷、推薦的名單以及推薦的原因——因為我相信所謂食物的力量,首先是關於「人」,而不僅僅是味道。《日本人的台灣美味》中有幾篇都在描寫這樣的時刻,〈永和豆漿〉較為直接,多數的篇章則是採取不同的角度。〈牛肉餡餅〉那篇就將兩個對於牛肉餡餅、看似無關的故事結合在一起,讓食物成為連結的橋橋梁。我到現在都能清楚地記得在中華商場後方,在鐵板上煎著肉汁橫溢油膩又美味的牛肉餡餅,以及國語教學中心的外省老先生,在餐館裡吃牛肉餡餅與我四目相對的情景,那是由食物所串連起的人,以及人的記憶。
在副刊剛連載時,我試著從不同面向去書寫食物,〈臭豆腐〉聚焦在外國人對於臭豆腐的抗拒與嘗試,在結尾處則加入人際互動的微妙之處。與其說以食物為主題,人情味才是作品的核心,我會觀察讀者的反應,發現這類型的作品讀者迴響更熱烈,這也表現了台灣人對於食物的情感投射。
又比如說〈麻辣火鍋〉那篇,寫兩位鬥辣的朋友,由於彼此的籍貫(一位是湖南人、一位是四川人)而不願在比辣上認輸,是為了表現出各地的口味、特色不同。人有著各自的口味,這涉及到籍貫、成長背景、甚至是私密的個人經驗,同樣的一道料理會得到不同的評價,這是非常正常的事——重要的不是品鑑食物的美味,而是我們同坐在一張餐桌上。《日本人的台灣美味》的特色之一,就在餐桌上對他人的觀察,而這些觀察又以一種趣味的方式說出來,我想這也是一種食物的力量。

Q 在日常生活中,你會時刻觀察他人來收集創作靈感嗎?
A 這幾乎成了一種習慣。寫作需要你有敏銳的觀察力,能從生活的小事裡找尋題材,身為一個來台灣生活的日本人,許多東西是我從未見過的,例如省籍衝突的問題,這對於其他國家的人來說是很難想像的;又例如統一發票,也是極具台灣特色的東西。我想創作就是去思考如何將一件小事改編成有趣的故事。每當我一有靈感,我會隨時記錄下來,事後再從這些零碎的靈感與筆記,重新編排創作,靈感是不會等人的。
Q 台灣人對食物的認同感很強,你覺得日本是否有類似情形?
A 日本人對食物的情感相對淡薄,沒有像台灣人有那麼深的認同感,當然各地有各地的特產,但像我自己是名古屋人,就沒有特別想推薦的名古屋料理。我很喜歡台灣的一句話——「嘉義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間火雞肉飯」,光這一句就代表了台灣人對於食物的愛,這是我很欣賞台灣飲食文化的一點。
前面問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構思《日本人的台灣美味》這個系列,現在想想,或許不僅是從拍攝YouTube影片得到的靈感,而是更早之前。我幾十年前來台灣,發現了那麼多你們可能習以為常的味道,但對我來說,那都是第一次見到、充滿驚喜的食物,《日本人的台灣美味》可能早從那時就開始了。
Q 「超級爺爺 SuperG」與《日本人的台灣美味》有相似的核心,不著重在食物,而是注重在一件件看似不起眼,卻閃閃發光的小事。能請老師與讀者分享你的口袋美食名單嗎?
A 這部分等到頻道系列結束後再公布吧!目前都是收集其他人的口袋名單,我想這個系列的最後一集,就是和大家分享我從別人推薦的名單中再選出的,我自己的名單。
採訪撰文|林佑霖
一九九五年出生,畢業於淡江中文系,東華華文創作所,現經營網路書店「昨日書店」。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新詩獎、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獎、後山文學獎現代詩首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現代詩首獎等;曾獲國藝會常態補助(文學創作類)、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著有《哀仔》。
攝影|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