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八年,黃裕邦帶著中譯詩集《天裂》在華語詩壇「出道」,該作不僅奪得美國LGBTQ文學獎——Lambda Literary Awards男同志詩歌組別首獎,其張狂的語言,挪用、挑釁文化符號的界線,真如書名般割開了詩歌的界線。時隔七年,黃裕邦帶來了第二本中譯詩集《微賤》,藉此機會,邀請裕邦來談談這本詩集以及這幾年對詩歌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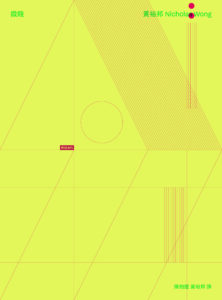
《微賤》
時報出版(2025.01)
《微賤》是香港詩人黃裕邦睽違六年的最新詩集中譯,部分內容選自入圍美國「Lambda Literary Awards」的《Besiege Me》,並收錄超過半數全新創作。詩集從一封虛構的婚禮喜帖開頭,探討家庭、陽剛氣質與酷兒身分,詩作在香港、台灣等地的城市景觀遷徙中,展現了詩人的私人情感與生存焦慮。
Q 《微賤》圍繞著一個敘事主軸——敘事者幻想在台灣與男友結婚,向父親發出喜帖,邀請他參加婚宴。這樣的設定帶有敘事性、戲劇性,在你設定的架構中,這會如何影響讀者閱讀詩集中的作品?
A 這並非是我特意設計或預先規劃了一個敘事主軸,《微賤》收錄的作品跨度從二〇一六年到二〇二三年,這些詩不是在一個明確的意念前提下書寫,而是慢慢累積起來的。可能因為這六、七年來的經歷與心境,使得詩集的開篇第一首詩〈請帖〉讓讀者有種被「邀請」的感覺——如果你出席我的婚禮,你會如何回應?不單純只是觀賞,而是進入一場想像中的儀式。《微賤》中有許多台灣元素,是從觀光客的角度切入:人們來到一個新的地方,既是旁觀者,又無法完全抽離——或許這也是閱讀《微賤》的一種角度。
Q 《微賤》沒有傳統的推薦序或推薦人,而是在成書前以低限的資訊徵稿,歡迎大家「描述、議論、推理、恭維、詆毀他們想像中的《微賤》」,徵集來的文字也經由改動/刪減,成為《微賤》的一部分。為何會選擇這樣的方式?
A 我的第一本詩集《天裂》是請相對不熟的人寫推薦序,但《微賤》比較私密,會期望書中所牽涉到的名字與文本,跟我的關係更長久、更親近,所以交由柏煜翻譯、睿哲設計。我不想用傳統的推薦序,而是選擇一種更開放的方式,把讀者的想像納入書中,成為這本書的一部分。這個做法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了「微賤」這個概念——它不是一個固定的、單一的形象,而是經由不同人的語言拼貼、刪減而成的。
睿哲和我並沒有對這些徵集來的文字做改動,而是直接收錄,讓它們與詩集互相對話。這讓我想到「刪減」和「拼貼」——像是詩集裡頭的一首詩〈把悲傷刪成gif〉,舊的文本它仍然在,但變成了新的形態。
Q 《微賤》的翻譯是由你和陳柏煜兩人共同完成,為了中文譯作的精確表達,甚至改寫了部分「原文」。你同時身為「作者」與「譯者」是如何在這兩個身分中切換?共同翻譯的過程又是如何進行的?
A 《微賤》的翻譯是我和柏煜在Google文件上共同編輯,柏煜會先翻成中文,我們再討論、修改,有時發覺某些詞句翻成中文後,感覺「不對」,甚至會回頭改原本的英語版本,中譯部分相當依賴柏煜對於中文詩的語感。
在美國出版詩集時,編輯有很大的權力去修改作者的作品,很多時候我無法決定英文詩集最終的呈現,所以在翻譯《微賤》時,我希望能保留自己真正想要的,也以更乾淨的語言去表達。
由於詩在英文的斷行方式與中文的節奏有所差異,翻譯有時必須調動字詞的順序,才能讓它讀起來更自然。我將柏煜的詩翻成英文時,也會根據英文詩的語感調整詩的斷行和節奏。


Q 《微賤》中收錄了你的視覺藝術作品,為何將這些作品與詩作並置?它們之間是如何建立相互對話的關係?
A 這些作品並非一開始就預設要收錄到《微賤》中,詩和視覺作品對我來說是一種相通的表達。比如說,我在書中用了三十六張圖,它們來自「把悲傷刪成gif」的概念,詩和視覺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對話,這本身是一個動態的創作過程。
我使用了水溶性碳,或將潤滑油與水彩混合,讓材質本身產生不確定性,這與詩的語言狀態類似——流動、不穩定、無法預測,詩是一行一行的排列,英文是line,這些作品中的「線條」也是詩。
裡頭有一些作品是我將退稿信重新抄錄在複寫紙上,抄寫那些編輯在退稿時所使用的固定的格式、制式的語言,使之與詩歌的開放性形成對比。這些文本並置在一起時,會產生新的關聯。
Q 距離你的上一部詩集《天裂》出版已經七年,《微賤》在風格、語言與書寫策略上都有顯著的變化。你認為自己的詩在這段時間內經歷了哪些轉變?
A 這幾年來,我仍然保持詩的「遊戲性」,但與《天裂》時期已經不同了,當時的書寫受當代美國詩歌傳統影響很深,對美國詩歌有一種想像。而這幾年,我對這種風格的興趣逐漸減少,現在我更希望讓語言流動,不去刻意模仿某種詩歌傳統。《微賤》更在乎語言的開放性,我不想讓詩成為某種固定的形式,而是希望它始終保持變動。
Q 《微賤》在語言上具有強烈的口語節奏,並大量運用跨文化的語彙,你如何看待這種混雜語言的書寫?
A 我一直覺得語言本來就處於一種流動的狀態,尤其對於這一代的香港人來說,語言的變動性可能更加明顯。我們成長過程中接觸大量的英語、粵語、普通話,以及來自網路和流行文化的詞彙,這些都成為我詩歌的一部分。
比起某種「純粹」的語言,我更在意詩的「遊戲性」,比如刪減、拼貼,甚至是對舊文本的重新加工。或許這些創作方式不見得多創新,但依舊能保持某一種創作的能量。同樣的文本交給不同詩人刪減,結果也會完全不同。我覺得這正是語言最有趣的地方,它不是靜態的,而是在不斷變動與再創造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可能性。

Q 你認為詩歌作為一種酷兒書寫的特質是什麼?
A 定義「酷兒書寫」應該是評論者或學者的工作,而不是創作者的責任。我對這類標籤化的討論相對排斥,尤其當這個議題變成某種政治討論時,往往會壓縮詩歌本身的空間。
但如果從詩的角度來談「酷兒」,我覺得它與詩的特質本身是相通的。詩是反叛的、游離的、無法歸類的,而酷兒的核心精神也是如此——它不是一個靜態的身分,而是一種動態的實踐。如果把「酷兒」當作動詞,那麼它就是一種行動,一種對規範的挑戰。
Q 組詩〈洞〉以各種角度去回應了香港移工的問題,在你看來,詩歌如何成為一種「介入社會」的方式?
A 詩歌本身的社會介入方式,往往不是直接的,它不只是一篇新聞報導或倡議。二〇一四年時,香港發生一起嚴重的虐待外籍移工的事件,在當時,香港有三十萬名外籍移工,幾乎都是擔任幫傭工作的女性,為香港製造了龐大的經濟效應,但一周卻只有一天假期,為了節約開支所以使用免費的公共空間,只能在維多利亞公園聚會。多年來香港並沒有解決他們的問題,去真正改善勞動條件。
創作〈洞〉時我人在西班牙,將隨手拿起的詩集以一種錯誤的方式翻譯,再將這些錯誤的、片段的小抄重組,有一些語言開始不是我的,而是透過一種自己不懂的語言所創造的真空,表達這些移工的處境。詩的介入不一定是直接的,我想它必須繞一圈,每個詩人能用自己的方式「繞」。
Q 你曾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生活(香港、台灣、歐美)及發表作品,你覺得自己的詩是否具有某種「跨文化」或「無國界」的特質?
A 我並不覺得自己的詩特別「跨文化」,因為我的書寫仍與香港有關,即使要試著「逃」出香港,但當你離開此地,進入另一個語境,必須首先肯認界線的存在——當我們談論「跨文化」時,是否已經預設了「文化」之間的邊界?但有時候,這些邊界是流動的、模糊的,甚至是被強行劃定的。
二〇二四年,我受邀參加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畫,我體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創作者如何交流與碰撞。在那裡,沒有人會因為你的出身而預設你的創作應該是什麼樣子。詩的元素並不完全依賴特定的語言文化,例如在《微賤》中,有三分之一的詩是近期創作的,有些作品本來是以英文書寫,再翻譯成中文,在這個過程中,某些詩句會因語言的轉換產生新的意涵,就已經跨越了某些看不見的「邊界」。
採訪撰文|林佑霖
一九九五年出生,畢業於淡江中文系,東華華文創作所,現經營網路書店「昨日書店」。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新詩獎、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獎、後山文學獎現代詩首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現代詩首獎等;曾獲國藝會常態補助(文學創作類)、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著有《哀仔》。
攝影|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