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與時代的對照:草間彌生與同時代的文學風潮
草間彌生,這位享譽國際的前衛藝術家,如今人們大多都知道她作品裡那些豔麗的色彩、無盡的圓點,以及南瓜,但其實她曾有長達二十餘年的時間,都持續地寫作、發表,留下數量可觀的文學作品,計有小說14種、詩集一種與自傳《無盡的網》。
若用文學史的角度回看,草間彌生出生的1929年,社會的不安與騷亂正蠢蠢欲動,華爾街經濟大蕭條的恐慌漣漪也逐漸蔓延至東洋。在這一年,小林多喜二發表了無產階級文學的重要傑作《蟹工船》,想藉此喚醒被資本家壓榨的廣大困苦勞工,而江戶川亂步寫下揉合官能慾愛及變態人性的短篇小說〈芋蟲〉,太宰治也嘗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與第二次自殺;隔年,川端康成則發表他早期代表作之一《淺草紅團》,以破碎的敘事描繪生活於都市底層庶民們目眩迷亂之悲歡。
不過,雖然這些作品反映了時代的混亂動盪,草間彌生卻並非浸淫在這樣的氛圍裡長大。相反地,根據自傳,她「活在一個非常保守的環境裡」,而在幼年至青春期間,她絕大部分的記憶,則是慘澹的家庭生活,以及自身的幻覺幻聽等精神病症。面對官能上的驚懼,年幼的草間彌生採用繪畫的方式(而非寫作)將這些感受、幻視畫面記錄下來,才讓心裡的感受得以沉澱,也是因此,她開始逐漸踏上藝術創作的道路。1957年,28歲的她前往紐約發展,因而接觸當時的嬉皮風潮,開啟更為前衛的藝術思想及創作歷程。就這樣度過16年,到了1973,由於身心狀況極度不佳,44歲的草間彌生從紐約返還故鄉日本就醫,卻因久病難癒,最後只好又定居日本。這段期間,她一邊接受治療,一邊挑戰各種新的創作表現手法,其中之一就是開啟文學寫作。
她的小說處女作《曼哈頓自殺未遂慣犯》出版於1978年,故事描繪紐約前衛藝術家的性解放生活場景,包含在當時仍屬禁忌的同性性愛、群交、屎尿癖等,以及角色在精神方面的強迫著魔傾向與自殺衝動,敘事中更寫到對日本藝術評論大師針生一郎、東野芳名等人的嘲諷,一般咸認為這是以她實際經驗為基底的自傳性作品。如此具爭議性的作品一出版,當然引起不少批評聲浪,不過要論她文學地位的確立,則要等到六年後(1984),第二本小說集《克里斯多夫男娼窟》的出版。
小說與詩的交融:草間文學的文類與文體
比較可惜的是,在臺灣,草間彌生的文學創作,僅有《克里斯多夫男娼窟》曾被翻譯,但目前已絕版。即使在日本,她的文學作品絕大多數也都已不再版,市面上少有流通;最常見到的,要屬自傳《無限的網》。這本自傳是她最新且最後一本文字作品;幸運的是,當中依照先後時序詳細羅列了所有文字創作的書名及出版項,若有心尋找,則可以按圖索驥。

《曼哈頓自殺未遂慣犯》封面
在前一年的1983年底,草間彌生以中篇小說〈克里斯多夫男娼窟〉獲得第十屆「野性時代新人文學獎」。這個文學獎由出版《野性時代》雜誌的角川書店舉辦,專門獎勵將作品發表在這本小說雜誌的新人作家。1984年,〈克里斯多夫男娼窟〉發表於該雜誌的一月號,而或許是受到激勵,在四、五月號上,草間又接連發表另外兩篇作品〈隔離布幕的囚犯〉與〈屍臭洋槐〉。同月,這三篇中篇小說很快地就被集結成冊出版。此後,她的寫作、出版活動便相當密集,平均每種著作出版相隔不到一、兩年,一直持續到2002年。
事實上,雖然草間彌生經常提及日本社會風氣保守,但在她開始文學創作並受到肯定的70年代後半至80年代,日本文壇的風氣、題材,都已逐漸邁向開放,例如受到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影響,女性作家開始湧現並更為活躍,其中包括與草間同齡或只有一歲之差的向田邦子及田邊聖子。而1976年,村上龍就已發表描繪年輕人嗑藥濫交的《接近無限透明的藍》並獲得芥川獎肯定;在草間發表小說處女作的那年,村上春樹也正在動筆創作第一本小說《聽風的歌》,並於隔年發表登上文壇。
可以說,時代的風氣與草間的文學創作,兩者遙相呼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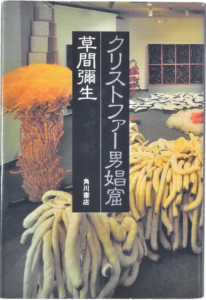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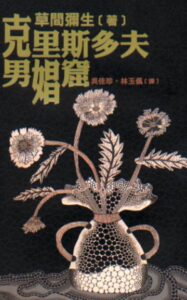
《克里斯多夫男娼窟》日文版及中文版封面 Cover of The Hustler’s Grotto of Christopher Street Japan (left) and Taiwan (right) editions
在自傳裡,她寫道:「對我而言,無論是用藝術來表現,還是用文字來表現,根本上是一樣的,兩者都可以開拓人類的精神領域」、「無論是創作藝術,還是撰文、寫詩和寫小說,都是我追尋自我的方式」;甚至她還這樣說:「〔按:文字創作和視覺藝術創作〕都是從心中漫溢出來的產物。小說、詩、雕刻、繪畫,一切的起源都相同。」這也的確落實在她的作品上。草間彌生許多小說、詩作的題目,與她視覺藝術作品的題名是相互呼應的。
比如自傳名的「無限的網」,就是沿用早期的繪畫系列名稱;而她現存最早的油畫作品《殘骸的積累(被人格解離帷幕包圍的囚犯)》,其副標題「被人格解離帷幕包圍的囚犯」(或譯「隔離布幕的囚犯」,兩者原文都是「離人カーテンの囚人」),也同樣延用於短篇小說,之後,她又以這個題目寫了一首詩。從油畫到詩作,前後相差38年,卻都繫於同樣的創作脈絡之內。然而,這些作品所表達的內涵、展示的樣貌,仍然多有差異,與其說是同一個母題的變奏,不如說是同一個母題的不同縱深、不同面向。可以說,草間的文學作品並不僅僅是視覺藝術作品的理念說明或註腳,而是她內在創作精神與意念的形式之一。
同時,她的文學作品還有一大特徵,就是散文語言與詩語言互相交融的文體。具體而言,比如自傳《無限的網》經常在生命經驗陳述到一半的時候,就毫無說明地插入一首詩作。這樣的狀況在小說作品中也偶爾可見,甚至,有些時候小說敘事的語言本身就帶有詩意,節奏短促,帶有自動書寫的傾向,語法上也常見扭曲、省略。比如《曼哈頓自殺未遂慣犯》的這幾個段落:「藥效已過,真是久違了。青色向胃的內側下沉,蔚藍色的天空只是青碧。早晨,現在,像是早晨。不可思議。天地的色彩,全都顛倒著」、「我是一個圓點。你也是一個圓點。還有一個圓點,是那位朋友。地球是一個圓點。太陽,是圓點的形狀。月亮也是圓點的形狀。」當中視覺意象強烈紛呈,一如她的畫作。
生之傷痕與死之徵兆在時間中舒展
草間彌生的視覺藝術創作,通常帶給受眾較為直觀的官能感受與衝擊,相較於此,她的小說、詩,以及自傳,則更清晰地描繪了其中的痛苦。尤其,小說敘事的本質,就在於時間流動所帶來的人事物之發展變化,所以更能交代前因後果,描繪生之傷痕如何造成,死之徵兆又是怎麼出現。
而這些,也就是她的文學作品不斷回應的母題。她的小說無例外地,氛圍盡皆陰鬱黯淡,往往充斥著扭曲的情感與人性、死亡、幻覺、強迫等,同時又滿溢著最暴烈赤裸的性描寫。但這些描寫卻絲毫不會讓人感覺行文的耽溺或者產生性慾,原因也許和草間彌生曾經大量製造陰莖狀軟雕塑的原因相同。由於她的生命經驗,對性與性器都充滿恐懼,但她卻不逃避,反而透過近乎偏執的無盡重複製作/書寫,直至自我消融,最終超克恐懼。或許這也是為何,在閱畢這些黑暗無光的故事之後,讀者卻又能隱約感受到一絲透明的、淡淡哀愁的抒情,彷彿企盼著靈魂的淨化或是解脫的到來。
比如〈克里斯多夫男娼窟〉,描寫一位異性戀的年輕黑人男性為了賺錢,在一位香港女性經營的男娼俱樂部底下工作,卻反受毒品與金錢的控制,只得被迫賣身給一位中年白人男性,直到他忍無可忍,揮刀斬斷白人男性的陰莖,最後卻走投無路,只能從高樓縱身一躍,變成一顆黑點。其實故事並不複雜,但草間彌生透過洪水般刺激性的語言,將這其中人性如何一步步變得扭曲,營造得令讀者感同身受。
又比如〈隔離布幕的囚犯〉,描寫一位少女紀子生長在扭曲的家庭,因父母之間病態關係的壓力影響,患上嚴重的人格解離與幻覺。這個故事同樣帶有強烈自傳色彩,應該有不少部分是取材自她在家鄉長野縣松本市的成長經驗,且較《無限的網》描繪得更為鉅細靡遺,更能讓人同理幼年的她的感受。不過,小說畢竟有虛構的必要,虛構拉開與真實的距離,才有空間讓讀者加入其中,所以也不能完全視這篇作品為自傳告白。仔細觀察,其中也有跳脫第一人稱視角的觀點去思考母親的處境,或是結尾紀子死亡的安排,也與現實不符。
相對於小說,草間彌生唯一的詩集《哀愁至此》(1989),收錄1975至89年間(包含曾出現在小說中)的詩作,其所呈現的面貌,可能更接近於她的視覺藝術創作,傾向直接表達、吐露感受,但是整體除了負向厭世及創傷痛苦的情緒之外,似乎多了一點點對家族的情感,以及對愛的欲求、對光明的渴望,以及溫柔。
例如詩集開篇的〈你留下幻覺的觸感〉末尾:「一步步踏著白雲刻印在地球的影子/來到野外去吧 拭掉淚水吧/花圈的觸感不知去向何處/我的淚水 也終將被雲之光曬乾嗎」,這當中表達了試圖超脫悲傷的心情。而與詩集的同名的詩作,則是以古典文言的語調詠道:「嗚呼 我已勞苦 宛若乞丐/屈身道旁 嘔出穢物/霜髮蓬頭 腰身佝僂/縱使老之將至 依舊不改冷眼/死亡要來則來 我仍會向宇宙出航」,這也有別於小說整體的樣貌,展現出內心崇高的追求。
在《克里斯多夫男娼窟》初版後記中,草間彌生寫道:「人類生存的模樣,邁向死亡的徵兆,愛的存在,生命的光芒與傷痕,還有宇宙那不可解的氛圍與充滿神祕的空間。時間。距離。——在這些背後高聳著的,究竟是什麼?」這段自述,或許最能描述她在文學創作時核心的關懷與思考吧。
本文原刊載於《草間彌生的「軌跡」與「奇跡」》展覽畫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北師美術館,2025)
撰文|盛浩偉
一九八八年生,臺北人,關注臺灣文史。著有《名為我之物》。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