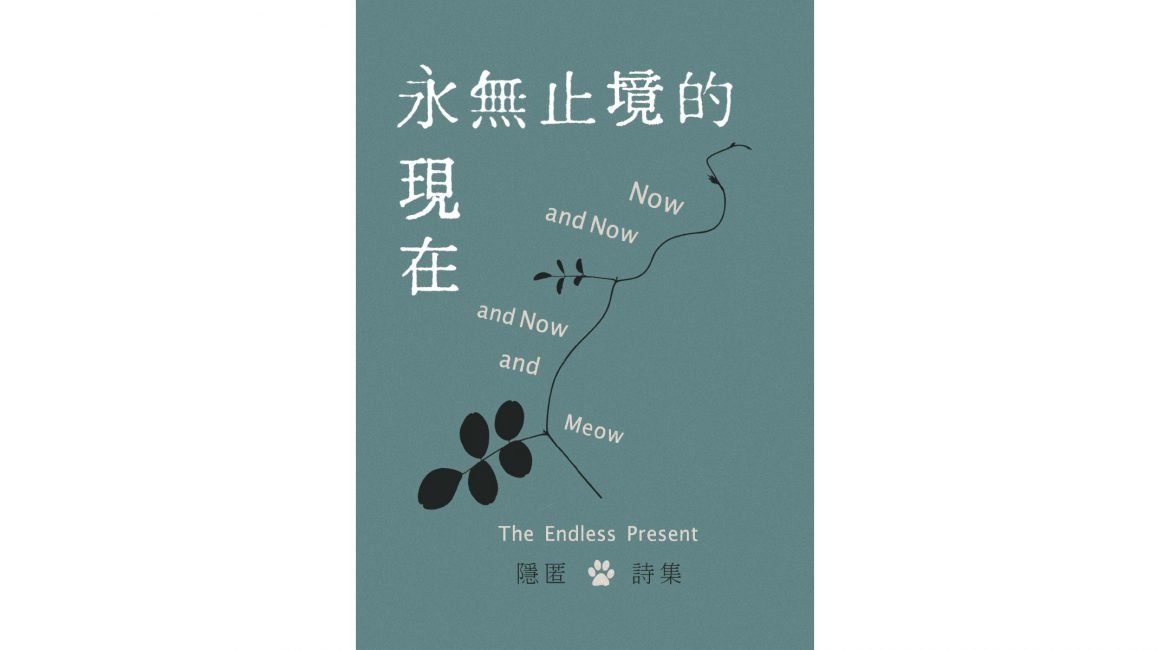只讀書名的第一眼,想到劇作家尤金.歐尼爾寫的台詞:沒有現在,也沒有未來,只有積累的過去不斷在當下重現。復沓嗎?但反覆注目著什麼,何嘗不可能釀出另一種凝視?
例如讀著《永無止境的現在》期間,翻出埋在家裡的《怎麼可能》。都讀過後,不禁屏息。這兩本書中間,隱匿究竟走了多遠的路?幾乎像是從以前在山頭上被夕陽的美震驚,到此刻逐漸能夠伸手撫摸雲朵與光線。
這是視野與理解的雙重延展:從被稱「厭世系」的否定對位、區隔人我,到描繪眾生景物間關係與秩序的底蘊,自己與這一切的聯繫與微眇,坦然地說:「在每一個我討厭的生物之中/都有微小的我(〈我不厭世只是……〉)」、「即使我/只是一團變動的/原子的聚合/我很抱歉/佔據了世界的/某個角落」。詩在區隔中創造了交融。
從這裡,書名暈開成兩層:永無止盡的厭世身心與挫傷限制裡,觀看出永無止境的風景,將自己安置其中。觀音何止是詩中閃現的山景,它還是「觀察世界的聲音」,是「觀自在」也是「自己的在」。「我只想真正理解自我的限制……唯有理解限制之所在,才可能理解自由。(〈詩/人〉)」可以說是這樣的願望嗎?書中隱約浮現的隱匿?
但隱匿不是不見。那些誠實到容易被視為銳利的視線與觀察,在某個句子的轉角,不時遇見。不願與寫幾首詩就自稱的詩人為伍、想踢所有低頭族的屁股或擊碎他們、並論場面話和真心話、談小燈泡事件……慈眉有時銳視,兩者在末尾詩輯的疾病和覺察中消融成一體。用符號「∞、∵、∂、⊕」作四輯輯名,不只是諷刺自己而已。記號受限於它的形體,卻可無窮繁衍,單純卻永恆,被賦予意義卻不斷傳遞派生。像詩,也像隱匿。
無盡/無境地置身於此刻,越走越深邃卻也越簡單的詩;看著周遭世界的同時,也(向內的)看見其中的自己;對萬物致歉的溫柔裡,有悉心包覆的慧黠與犀利。這份視野與今昔併讀的過程,令我時不時分心想到《黑色的歌》。冒著誇大的風險說:儘管不是每首詩都如此,但在其中有些詩裡,讀者會感到彷彿隱匿跟辛波絲卡正走在同一條小路上,一起朝向某個無法望盡的地方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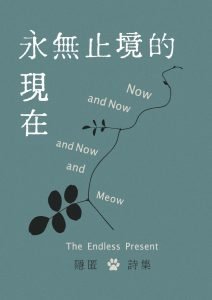
《永無止境的現在》
隱匿 著
黑眼睛文化
延伸閱讀
傳說中辛波絲卡的第一本詩集,塵封多年成為作者逝後的「新書」。由林蔚昀自波蘭文直譯,取相同主題的晚期詩作,今昔對照並解析。青年詩人對世界的覺察與熱情、熟年詩人視野的開闊深邃、不變的對戰爭、女子、人性的深究與諒解,和新生代詩人譯者的回眺啟示,在《黑色的歌》中交錯映照成三稜鏡內外多彩明暗的視界——序詩中描述「我曾經是的女孩」的女子(看起來)在跋詩中見到了過去的自己。詩集內外,對照與相遇無所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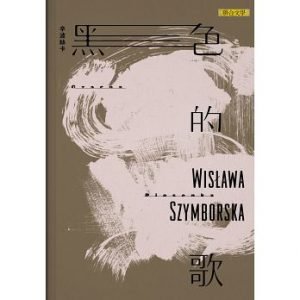
《黑色的歌》
辛波絲卡 著
林蔚昀 譯
聯合文學
譚洋
東華華文所創作組畢,從報社、書店漂泊到海上。現為蘇帆海洋基金會獨木舟志工教練、黑潮基金會海上解說員。寫字,學划獨木舟,有時海泳。活在東岸,以後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