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內的密室出現以來,它逐漸不只是一整體的空,而開始浮現出內在的不均質。於是這個空就像一小塊海洋,有浮游生物濃淡的變化,有人造的漂浮物,有高低層的生態。而不是像一小包成分被嚴格管控製造出來的生理食鹽水。但他人是空,有灰階的空。」與張惠菁說話,隱隱感覺穿越拱廊,沙粒掉落。空氣中有嗡鳴,那好像是時間本身的沙沙回音。她說,我有好幾個時間,而我的書寫是與我的時間平行。事實上,所有的書寫都與它的時間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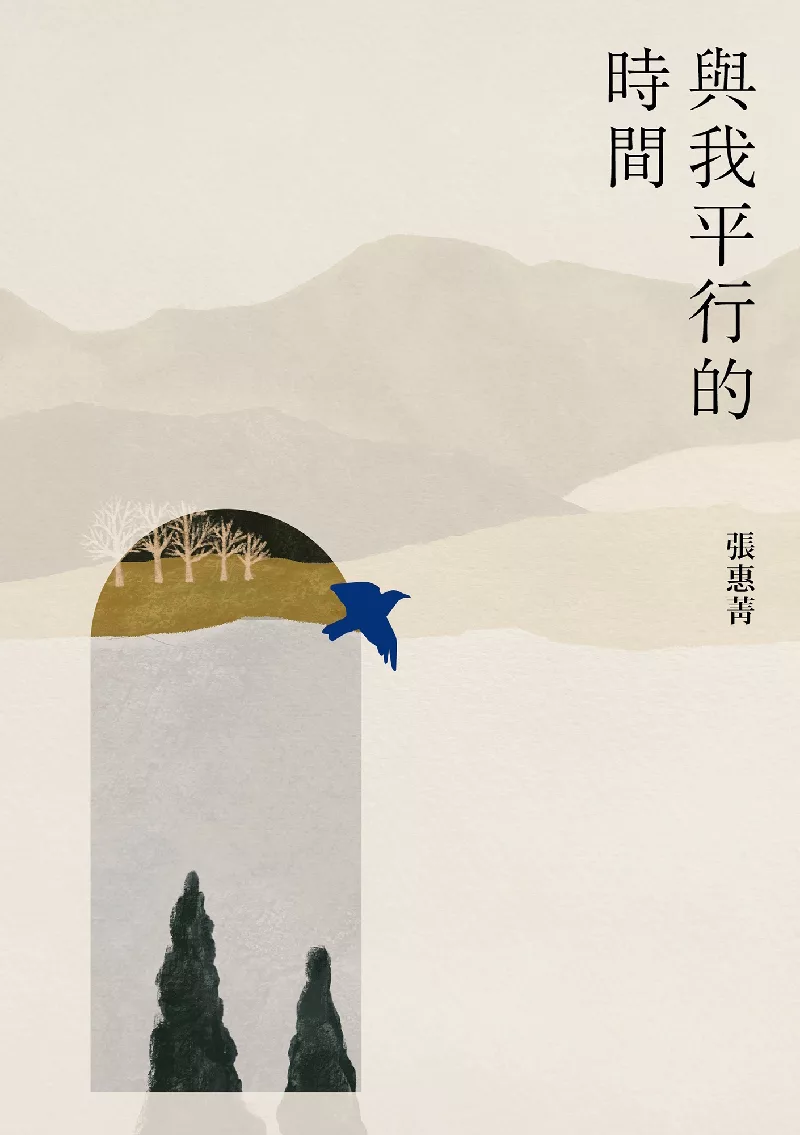
《與我平行的時間》
遠流出版(2025.02)
睽違六年,散文集《與我平行的時間》延續張惠菁對時間與自我深刻的探索,展現出更為成熟與細膩的書寫風格。透過日常觀察、閱讀筆記與內在對話,描繪出多重時間與自我交織的意識景觀。以詩意的語言,呈現出「我」在不同時間軸上所經歷的感知與情感,並探討時間的非線性本質。
Q 惠菁的文字讓人聯想到雲層緩緩掠過山脊的光影變化,在柔和的調性中,細節逐漸顯現。對你而言,散文的書寫是一種回溯既知的經驗嗎?
A 我覺得散文一定是有已知的部分。很可能你從一個已知的事物開始寫,但是將自己開放給敘事,在後來逐漸揭露出未知。這是寫作對我來說最有魅力的地方。差不多就是寫《告別》的時候,我開始發現,散文對我來講有這個魅力。有可能我從一個點開始寫,但在敘事的過程中,更多覺知得以展開注意到一些我原先沒有想到的事情。我之前寫了一段時間的專欄,專欄字數大約是兩千字,這個篇幅對我來說有點像一個內觀的過程。常有讀者說,說:「你的文章經常前面在講某件特定的事,忽然出現轉折,浮現出一個結論。」為什麼會有這個轉折?有時就像是在寫作中內觀自然出現的。在寫的過程之中慢慢有辦法去察覺原本未知的,對於新生的覺知,以文字賦與它形狀。
Q 你的語言風格相當清晰,其中蘊含著明確的敘事意志。這樣的意志在你早期的創作中就已經成形了嗎?
A 這好像是一種微妙的界分。我喜歡的散文,你能讀到敘事的意志,但不是宣言、不是邏輯論理,在寫的過程中很可能充滿探究與模索,而不是封閉、預設、刻板的結論。這次書中有一篇文章叫做〈一場好探索〉,就是在談這種感覺,因為寫作者有前進的意志,才會有探索;但探索又是敞開與溝通的過程,把自己開放給文字帶來的展開。
Q 在我的心目中惠菁是一個小說家。很多時刻,你的語言會呈現出小說的質地。你如何看待小說這種形式在你創作中的位置與意義?
A 我自己閱讀很多小說,但是關於你說我的語言呈現出小說的質地,這點我倒沒有特別想過。無論小說與否,釐清「自己想講的故事是什麼」這件事情還是比較重要。我現在有時候也會想(寫小說),但目前還沒有進行下去(笑)。


Q 你提到與故宮有關的那段經歷,我是近來才第一次聽到。從讀者的角度觀察,那似乎成為你書寫轉向的某個節點,其後你的語言似乎變得更為堅定而清明。你自己是如何看待那次經驗對書寫的影響?
A 對我來說,那個官司本身確實給了我很大的衝擊。當下那種巨大的、強烈的不安感,我在那篇文章裡都有寫到。在司法調查的場域裡,我原本習慣的表述方式,句子可能確實是比較長,有比較多的說明,當時曾經被多次打斷。這個經驗讓我意識到,原本以為只要照自己習慣的方式,真誠地說明,就可以被理解,這個想法其實是很奢侈的。很多時候,為了讓人理解,必須努力地整理自己,必須費心整頓句子,思考自己和對方之間的共同語言。人和與自己不同的人之間,溝通其實是很困難的。如果溝通不攸關生死,可能可以選擇不和對方說話;但如果攸關生死,或像我必須為自己辯白,就必須努力使用語言。
那個時候就突然意識到,覺得原來做一個寫作者時,我是幸運的,文學的領域裡,自我的表達是被尊重的。但法庭的經驗和我後來的社會經驗,讓我意識到,拓寬自己溝通頻道的重要性。當溝通對你重要的時候,你就非得要嘗試找到方法,而不能只說自己習慣說的話。你會在溝通不成功的時候,後退一步思考,進行語言的整理,然後再嘗試,如此不斷循環,漸漸地溝通方式就比以前拓寬,但也沒有失去原本的自己。所以我們做為人,不只是一條單行道,而可以是個光譜,可以保持這個覺知。
Q 在你的文字裡,偶爾可以感受到類似冥想或內觀的節奏與痕跡。這樣的實踐經驗是否對你的書寫啓發?
A 有幾年,我花比較多時間在修行上面,每天做功課。現在雖然沒有持續做功課,但佛教的世界觀很自然地影響了我。這個世界觀怎麼講呢,要說的話可能就是「多元」——我看待時間、看待自我,是以一個比較多元的狀態。如果你去看唐卡,你會發現裡面有各種各樣的存在與視角。在佛經裡,也有各種的境界與狀態。人本就是只是宇宙中一種微小的生物,在我們的身周,隨時存在著更多有形無形的物種,天龍八部,天人阿修羅,地獄畜生惡鬼⋯⋯我們在這多元的世界中修行。
我也感到,事物行進的路徑,不是只有有形的邏輯。或許有些人有這樣的經驗,在看似沒有辦法的時候,打坐、或者靜心後,有些解法會自動浮現。這就好像人與人之間、與萬事萬物之間,存在著相通的地下室,以看不見的地下通道相連接。有時不是透過有形的言語、論據,而是在一種更大的共時性中相互對應。
活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世俗的事情要處理。但我喜歡想成,我們都擁有許多平行的時間,這些時間,即使在我們沒有意識到的時候,也仍然在積累與沉澱。如果眼前的這個人,我們感到現在無法理解,他未必永遠是如此的,正如我們也不是永遠不變。或因為我現在看到的也僅是他現在的樣子,而我也在我自己的時間中經歷著變遷,我們有各自熟成的節奏。理解這一點後,去看見自己身內與身外,世上存在各種時間、各種生存狀態,這就是「與我平行的時間」這個書名的由來。或許就像芙莉蓮一樣。

Q 你如何理解閱讀這件事?除了作為工作或興趣之外,閱讀在你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如何?你會如何安排與分配閱讀的時間與內容?
A 很多人說,看我臉書會覺得我怎麼有空看那麼多劇和小説,明明很忙!但正是因為忙,所以常常需要閱讀和看劇。有些作者總是沒有讓我失望,比如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就沒有讓我失望過,我很推薦《黑暗的左手》和「地海系列」。我讀「地海系列」的時候是我人生比較低谷的時候,當時正在經歷官司,也有一點中年的焦慮,覺得生活狀態充滿不安,但意外在「地海系列」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第一集跟第二集主角,第一集故事裡的男巫師其實有點驕傲、對自己的力量太過自信,於是犯下一個錯誤,他在嘗試去補救的過程中,逐漸對自己產生新的認識;第二集的主角是一位女性,從小就被關在古墓之中,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而她離開這個封閉的世界。這兩個故事都非常觸動當時的我,好像與我那時候的狀態有所映照。在地海的世界裡,力量並不是一個絕對的事物,鄉野的小法術有大巫師解決不了的謎團,女性或受傷者可以顛覆建制。那個世界觀不是英雄主義式的,非常柔軟。我相信勒瑰思一定是個有地下室的人,或者你可以清楚知道,她去過那個地下室。
Q 在《與我平行的時間》中,對時間的描寫有時呈現出非線性的、帶有質感的塊狀意象,像是被鑲嵌於文字間的微粒。你如何看待抽象性在文學書寫中的位置與可能?
A 它其實是自然出現。我相信很多寫作的人都有自己非常關切的問題,那個主題之後會一直反覆地出現在你的寫作中。寫散文的時候,我覺得關鍵的主題是:世界作為一個謎題,自我作為一個謎題,我經常經歷著它的神秘,也想書寫它的神秘性。世界作為現象可能會改組,也可能隨時翻轉,我想寫我所經歷的此刻、和在當中變化的時間。李桐豪讀完這本新書之後跟我說,覺得我的「身體」不見了;也有人說,現在的語言比以前更簡單、直接。這些都是自然發生的,我並沒有刻意做什麼。
這應該就是跟我當下的生活有關吧,非常奇妙,有時候你會忽然感受到內在存在著一個空間。雖然現在直接吃到一塊美好的戚風蛋糕也是非常好,但直接描寫戚風蛋糕可能不是我現在想描做的事。我可能會比較想寫發現、覺知到內在空間的那個當下,想寫那種非物質性的感受,比較抽象的,但也更不容易描寫。啊,但是戚風蛋糕也有可能引發剛剛講的那一切。

採訪撰文|蕭熠
八〇年代生於台北,畢業於芝加哥藝術學院,紐約普瑞特建築碩士。曾在芝加哥,紐約,香港求學生活。曾獲台灣文藝營小說類首獎,林榮三文學獎、台積電文學賞入圍,《107九歌年度小說選》入選。作品散見各大副刊及《印刻文學生活誌》等。現居台北,持續生活寫作。著有小說《名為世界的地方》和《四遊記》。
攝影|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