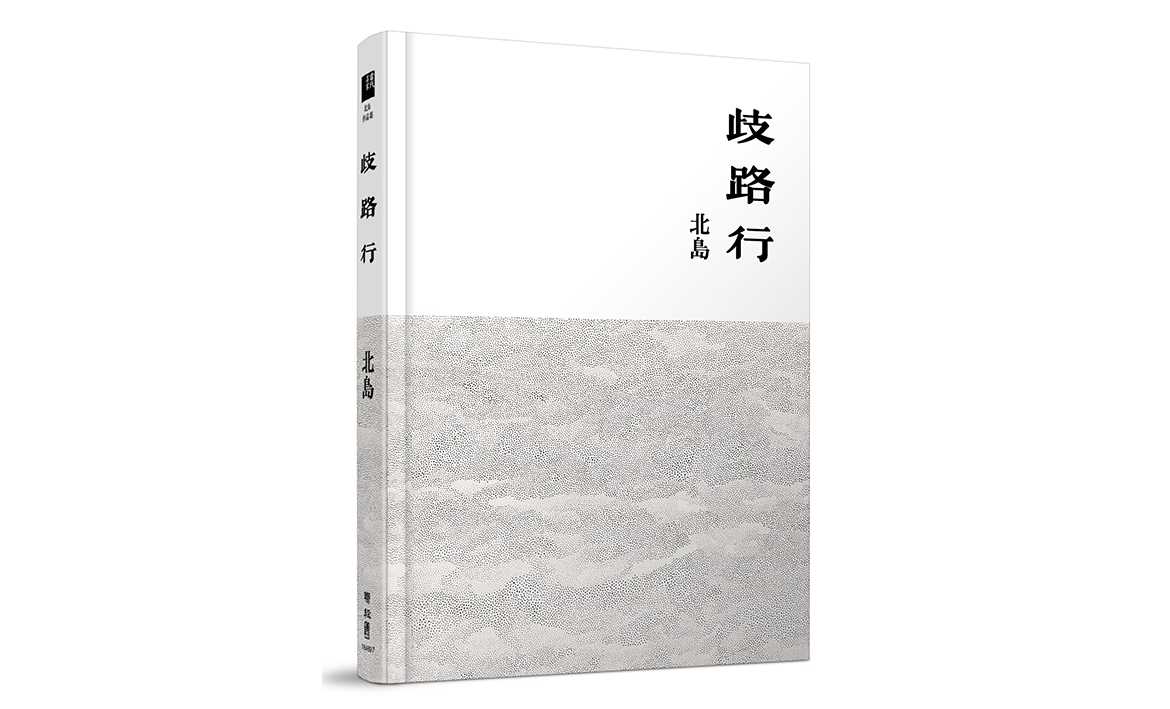本文摘自「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粉專,原文連結。
歧路行.第一章◎北島
⠀
逝去的是大海返回的是泡沫
逝去的是一江春水返回的是空空河床
逝去的是晴空返回的是響箭
逝去的是種子返回的是流水賬
逝去的是樹返回的是柴
逝去的是大火返回的是冰霜
逝去的是古老傳說返回的是謠言
逝去的是飛鳥返回的是詩行
逝去的是星星盛宴返回的是夜的暴政
逝去的是百姓返回的是帝王
逝去的是夢返回的是歌
逝去的是歌返回的是路
逝去的是路返回的是異鄉
逝去的逝去的是無窮的追問
返回的沒有聲響
⠀
我是來自彼岸的老漁夫
把風暴的故事收進沉默的網
我是鍛造無形慾望的鐵匠
讓鋼鐵在淬火之痛中更堅強
我是流水線上車衣的女工
用細密的針腳追尋雲中的家鄉
我是煤礦罷工的組織者
釋放黑色詞語中瓦斯的音量
我是看守自己一生的獄卒
讓鑰匙的奔馬穿過鎖孔之光
我是年老眼瞎的圖書館員
傾聽書頁上清風與塵土的冥想
我是住在內心牢籠的君王
當綢緞從織布機還原成晚霞
目送落日在銅鏡中流放
⠀
是晨鐘敲響的時候了
是深淵中靈魂浮現的時候了
是季節眨眼的時候了
是花開花落吐出果核的時候了
是蜘蛛網重構邏輯的時候了
是槍殺古老記憶的時候了
是劊子手思念空床的時候了
是星光連接生者與死者的時候了
是女人在廣告上微笑的時候了
是銀行的猛虎出籠的時候了
是石頭雕像走動的時候了
是汽笛尖叫翻轉天空的時候了
是時代匿名的時候了
是詩歌洩露天機的時候了
是時候了
中國當代重要詩人北島在2010年開始了長詩的寫作,12年過後,三十四章的《歧路行》在2022年於香港出版(台灣版也在2023年2月由聯經出版),這本詩集可以視為73歲的北島,對過去的詩歌生涯和命運種種的回溯,把人生的線索收束,召喚詩歌裏曾一度隱藏的幽靈,與之迴響。
北島詩歌的意像空間多元複雜,他的遷移經歷、外文詩譯介所回饋的養份,乃至「北島」作為一個政治文化符號,都使他的作品擁有多重的解讀方式。從詩歌偶像到80年代「pass北島」的口號,他的影響力依舊強大,而在眾聲喧鬧的評論聲裏,晚年北島給出的答覆則是:歧路。在正道之外,岔途而不復返,他的北京、他的香港、他所目睹過的世界,都成為了一種迂迴的路線。讓我們先順住他的歧路,投石問路之際,石頭會在猝不及防之時回擊我們。
/
鄭政恆在〈人生實難,大道多歧:北島《歧路行》章回評〉一文中,為富自傳色彩的《歧路行》,系統性也疏理出每章節所對應的歷史與典故,以及其中幽微的視野轉換,並援引張棗「詞的流亡」的說法,指出:「《歧路行》當中比比皆是的流亡話語,也切合北島在詩中呈現的自我陌生化。大大小小的歷史事件和個人經驗,都經過陌生化的處理,並重新呈現出來,教讀者以新的眼光去面對個人史和當代史。」
《歧路行》的〈第一章〉可以視為北島對其個人詩歌史,敲出的一則迴響,風暴、夢、晨鐘.劊子手等等,都是他最廣為人知的標誌意像,更熟悉北島的讀者甚至能把每一行句子,與舊作扣連。然而呼喚幽靈,不會單純是為了耹聽它們重述自己的淒淒慘慘,在第一節「逝去的是A返回的是B」的句式下,詩人更像是朝它們開了一槍,讓逝去的字詞再死一次,使之復活 。那些在北島流亡生涯寫下的意象A,被不同的邏輯變化成了意象B,其中的邏輯包括自然法則、人為變動、物件性質的異變、詞性變形、外在形象的譬喻修辭,既是詩人的回望,也是詩藝與詩境的展示。
其中幾句從「歌」到「路」,再到「異鄉」的複沓變形,較為重要,參考黃子平對北島詩作的說法:「語詞與道路的精警組合,構成北島近年詩作中(按:黃文寫於2005年),歷史情境與個人情境最密切交織的關鍵意念。」然而在本作中,路卻通往了異鄉。當無窮的追問逝去,而沒有聲響返來,詩人才回過神來,發現其實消失的東西,並沒有真的變化萬千。所以「路」沒有最終成為「故鄉」的正途,復活的儀式失敗,那麼他所構造的歷史情境與個人情境,也受到了威脅,變回流亡的詞語。
所以在第二節中,「我」便要化身為不同的角色,成為統領眾多意象的把控者,即使在困境裏也絕不頹唐,要「把風暴的故事收進沉默的網」,也要「釋放黑色詞語中瓦斯的音量」,把流亡的的詞語穩固下來。即使當故鄉出現時,「流水線上車衣的女工/用細密的針腳追尋雲中的家鄉」,暗示了詩人其實自覺地意識到,家鄉猶如在浮雲中,可見而不可觸,但鄉愁在詩行中卻是受控的,就算「住在內心牢籠」,我也是自己的君王。
接承前述兩節的意象,第三節也借助「是XXX的時候了」的句式,將北島過往的詩作翻轉,讓詞語完成它們真正的復活。此部分意象變化的策略,大多是回溯,像「花開花落吐出果核」,把盛放與衰敗的生命輪迴,歸返到一切起源;也像「劊子手思念空床」, 把殺戮擲回初生的虛空。詩人的氣魄最終展現,無論是神話掌舵的朝代,還是資本發達的時期,這些時代都要匿名下來,讓位給詩歌──〈第一章〉在此結束,但這意味住接下來,北島是時候要開始講他真正要說的話了。
/
時間回到1989年,北京爆發連串的民主運動,北島發聲支援,六四事件爆發後,當時身處海外的北島開始了流亡生涯,直到近二十年後的 2007年,得到香港中文大學任聘,才定居於香港。
當61歲的北島開始《歧路行》的寫作時,〈第一章〉的詩句展示了他對這首長詩的野心和企圖,正如他要先「槍殺古老記憶」,才能用「蜘蛛網重構邏輯」,最終極有氣魄地說:「詩歌洩露天機」。在寫作長詩的過程中,北島曾經中風,語言程度只餘下三成,而他在訪談裏的回應是:「我不信所謂科學的判斷。可以說,這是我對命運的又一次抗爭,也有對命運好奇的成分。」詩人對待命運,不單單是對抗,更是好奇,而好奇的下一步呢?也許是解構、重組,最終試著去掌握。
接下的各個章節,詩人都展現了他如何與命運搏鬥,穿梭於不同時空,寫人寫事,寫記憶的大小虛實,種種歧路的風景誕生了如今的北島。也許,我們可以先跳到這段路途暫時的落腳點,看看在《歧路行》最後的「第三十四章」,北島如何處理他居住了近14年的香港。那裏會是異地?是新的故鄉?還是歧路上一點靠近歸途的亮光?
我們下篇再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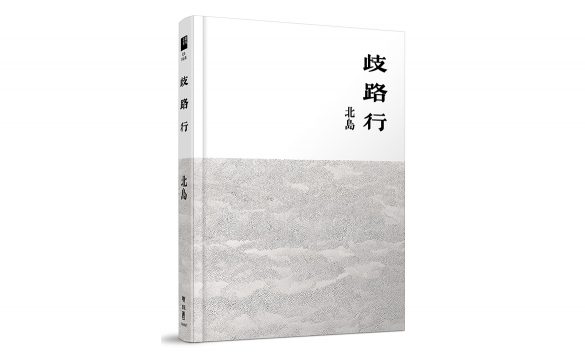
《歧路行》
北島,聯經出版
文|韓祺疇
生於1996年,畢業於嶺南大學中文系。曾獲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大學文學獎等。